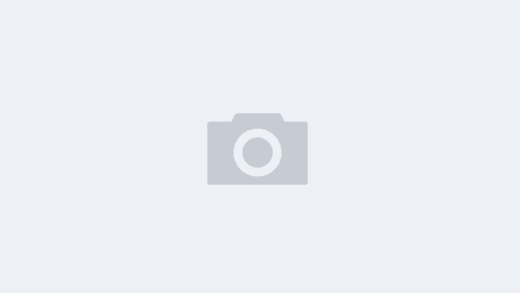我是9月16号新生报到的最后一天去的学校,因为就在前一天,父亲才凑够了我的学费。那天村外的路很滑,我背着母亲用绿布缝制的背包,身上是姐姐撕给母亲她一直舍不得穿的灰布做成的短袖,在风中簌簌扇动。我曾经以为那很好看,但当我站在如潮的人群中,被一片鲜艳的色彩包围时,我和父亲只能局促地蹭着脚上的泥巴,不知所措。
交费的队伍如长蛇一般逶迤前行。父亲紧攥着怀里的钱,我靠在旁边的柱子上,羞涩而又新奇。快中午的时候,队伍只剩下我们两三个人,父亲的一只手还在怀里。忽然,父亲惊叫一声:“抢钱啦!”我的心剧烈地缩了一下,看见一个年轻人很快窜出大门。我也跟着大声喊:“抓贼呀,有人抢钱啦!”
其实人在遭遇罪恶的时候,心头的第一感觉是恐惧,第二还是恐惧。我和父亲那一瞬间居然都没有动,而是愣在那里。等我们醒悟过来,那个贼已经被校门口一圈人围住。我们分开人群,他摔在地上,额头下面一摊血。边上一个四五十岁的中年人蹲在地上,默默地捡撒在地上的西葫芦。
人们都在议论纷纷:“多亏你们俩运气好,这个贼恰巧撞到了张师傅的三轮车上,要不你们的钱非被抢走不可。”还有人说:“张师傅,你这不是故意撞他的吧?那你可要算是见义勇为了。”那个中年人头也没抬,闷声闷气地说:“别抬举我了,这一车菜撞坏了老板是要骂的。”保安出来,架着贼去了派出所。父亲拿出100块钱要塞给他,他看也没看:“你这是做什么?你很有钱吗?赶紧给孩子交学费去吧。”说着,他一瘸一拐地推着三轮车走了。
这时,我才看见,他的裤子被撕破了一个大口子,他把上衣往下拽拽,冲我笑了笑,哼着“想当年老夫我身强力壮,身穿盔甲我手持银枪……”消失在绿阴笼罩的校园深处。
我蓦然想起来,由于不懂世事的害羞和慌乱,我居然连一声谢谢都没有说!我所知道的就是他姓张,如此而已。但在这上万人的校园里,重逢的机会又是何等地微乎其微!这样想着,我心中怅然若失。尽管我来自农村,长辈很早就教会我懂得感恩,懂得欠人家的要补偿,要发自内心地去感激。
可我没想到找到他是如此容易,仿佛许多人都和张师傅很熟一样。我问一个高年级的学长,他说:“你说的是学三食堂的张师傅吧,光着头,见人一脸笑,一副马大哈的样子?”我说大概是吧,我也不认识他。然后他领着我,到一个队伍特别长的窗口,排到跟前,果然是他,穿着一件蓝大褂,光着头,显得十分滑稽。
他对我笑了笑:“你父亲走了?没留他在这儿吃饭?”我摇摇头,缓缓又点点头。他挥着一个大勺子把我的饭缸打满,说:“你先去吃吧,吃完了还在这儿打,记住了吗?”那天中午,两份1元5角的米饭,我和父亲都吃得饱嗝连连。而张师傅,成为我大学时代第一个没有任何自卑与不适的朋友——曾经,我把他当作长辈,但很快就忘了。
张师傅很爱笑,整天脸上都是笑眯眯的。总看见他的同事们往他头上、脖子上乱摸,他也不怎么躲避,更谈不上生气了。后来学校给我提供了一个校工的岗位,每次开饭完毕打扫餐厅的卫生。看见我蘸着水一遍遍在地面上拖,他说:“你呀,不能这个样子。应该先干着拖几遍,最后蘸水才能拖干净。”我说:“那你给我示范一下吧。”他果然就来回在餐厅里拖,我蹲在门口看来往的人群。
往往他拖净了,喊我:“哎,看见没有,就是这样拖的。”我笑着转过脸:“我什么也没看见。”他假装生气地摔下拖把,很快他就又笑起来:“你这个坏学生,你在骗我,是不是?”我也笑起来。下一次,他还会抢着拿起拖把。
大二时,我喜欢上了一个女孩,她也说她很喜欢我。我告诉了张师傅,想让他和我一起分享喜悦。另外,当然还有一些炫耀的成分,我知道他一直没有结婚。他说,这样吧,你让她来帮你拖一次地,让我看看她漂不漂亮。我对那个女孩说吃过饭我们在餐厅见一面,她很疑惑,但还是点点头。
她穿着洁白的连衣裙走进餐厅的时候,我正一身泥水、满头大汗在拖着地。我扶起拖把对她笑了一下,她也笑了一下,但还是后退了几步,也很勉强。
张师傅在旁边说:“姑娘,你替他拖一会儿吧,他还没吃饭呢。”她在湿漉漉的地面上走了几步,白色的鞋上很快溅上了几滴泥水。她皱着眉头,目光看着门外。张师傅接过我手里的拖把,往远处拖去,很远地叹出一口气。
我俩看着池塘里的荷叶。青翠的浮萍中有蛙声传来。我说,你听见青蛙在说些什么吗?她没有看我,说,我要去教室里自习了。说完噔噔离去。我说,你不等我吗?她停了一下,还是继续往前走去。我听见张师傅又是一声叹息。
那天晚上,我第一次喝酒。在张师傅那狭小的吊着黄晕灯泡的宿舍里,两包花生米,几瓶廉价的二锅头,我们很快都醉意朦胧。他劝我:“小伙子,千万别太往心里去,否则就成了一个魔鬼,永远躲在你心里,吐都吐不出来。”我抬起头:“怎么,你也曾有这种感觉?”他叹了一口气。这时借着昏暗的灯光,我看见他的脸上晶莹——那是他的泪。
我第一次看见总是笑呵呵的他居然也会掉泪,想也想不到。“那还是我在西藏当兵的时候。离哨所不远是一个牧民定居点,那儿有一个叫嘎娜的姑娘。她的牙齿像雪一样白,她的身子像刚绽出的柳条一样柔软。她喜欢唱歌,尤其是月亮升起在雪山上空的时候,她的歌声,如夜莺一样在枝头山间掠过。我们每个人都醉了,比现在还要醉……
“嘎娜每次看见我,总要羞涩地低下头。战友们都取笑我说她喜欢上我了,我每次都擂他们一拳,可是我的心里,却像吃了蜜糖一样甜……在梦里,我梦见嘎娜站在大片的花丛中,对我微笑。我想折下一枝送给她,却又不敢……
“嘎娜有一天送给了我一个小刀,刀柄上刻着两条纠缠在一起的蛇。我知道那一定代表着什么,可军人的职责不允许我多想。我经过了好长时间的斗争,最终,我还是把它交给了班长。交上去之后我就后悔,可一切都太晚了,班长直接去找了她的父亲……
“嘎娜再次见我的时候,红红的。我拦住她,想要说些什么,她也在等待。可许久之后我还是没有说话,她就一把推开我,冲了过去。我撵上去,她狠狠骂我一句:胆小鬼,算什么男人!我愣在那里,风裹着沙子砸在我的脸上,我毫无知觉……
“不久,嘎娜出嫁了,她父亲收了别人30匹马的彩礼,把她嫁给了一个死去妻子的老男人。出嫁那天,嘎娜的哭声在哨所里都能听到。听说,好几个女人都摁不住她,她跪在地上,大声呼喊着我的名字。而我,正被班长关禁闭,无声地流着泪……”
我的脸上不知什么时候也有虫子爬呀爬。我问他:“那你以后就没有再去找过嘎娜吗?”“复员那天,我想去找她,可我一想,爱一个人,不一定就要在一起,默默地想念不也挺好吗?”我明白了,这么多年张师傅一直坚持独身的原因。
“那你感到幸福吗?你知道嘎娜幸福吗?爱一个人,一定要表白出来,一定要让对方幸福,否则,那就是一种伤害。你知道吗?”我一口气说了这么多,剧烈地喘着气。他奇怪地看着我。“嘎娜说得没错,你根本就不是一个男人!”撂下这句话,我气呼呼地走了。
1年之后,我凭打工的收入基本上够支付自己的学费和生活费,而真正爱我的那个女孩,和我一起并肩拖地、并肩练摊。我们已经跟张师傅商量好,趁假期去西藏寻找嘎娜,如果找到,就真诚地说一声对不起;如果找不到,就听我俩的安排,老老实实地成家。因为,真实的生活,不仅仅是等待和怀念。追求与创造,才能不再让生命中留有缺憾。
文章来源于互联网,如有版权问题,请联系客服删除处理。
同意孩子早恋、支持孩子高消费……对于广州不断出现的新潮家长的教育观念,众多资深中学教师表示担忧。老师们指出:现在很多孩子吃苦耐劳性差、不懂得节俭和谦让、没有责任心,这与一些家长的“新潮”观念有很大关系。 位于广州五山的某中学老师告诉记者:在一次课外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