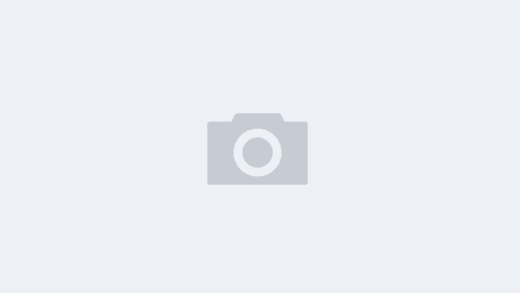来自于官方的宣传话语,在一些“开明人士”看来,是不值一提的废话和谎言。而最让人不解是,这样的废话和谎言,从表面上看来同社会的快速发展似乎并无太大抵触。也许我们可以笑对《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或者恶搞一下《新闻联播》,但无法否认这些极权主义式的宣传话语仍具有非凡的社会效应,它塑造了一代人,并仍在努力塑造另一代。在这个被称为“后极权主义”的时代里,官方宣传话语还将持续某种程度上的影响力,它的本质并不随着经济自由化而改变,相反,当GDP和个体的孤立感、焦虑感同步骤增时,这些原来食而无味的宣传话语,呈现出了“供不应求”的局面,以至于回顾这几年,竟发现官方宣传话语像时尚一样不断地翻新:“代表”、“盛世”、“伟光正”、“和谐”、“八荣八耻”、“和平崛起”……也许并不能把这些完全归咎于极权主义的残余,而更应该将其同我们这个的时代的普遍特征DD“焦虑感”联系起来;这些索然无味的符号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DD对焦虑的无意识抗拒。
词一:人民
“人民”被强行嵌入各种名词之中,与其说是作为定语,倒不说是对其后的名词进行一种再诠释,防止这类词汇及其所涉及的焦虑影响到人们的基本世界观,由此,这些名词被彻底地“去实义化”了。
例如,在“人民法院”中:“人民”一词实质上被用来削弱和抵御由“法院”的真实含义上的文化不适所带来的普遍焦虑感。“法院”,作为一个能指、一个与日常经验相脱离的符号,它被强行推介给了个体,但词语仅就其本身而言是无法勾起个体对正义、公道这类概念的关联性想像,它只是一个游荡着的、悬置着的能指,等待某种可理解的所指的出现。一旦对“法院”一词进行理性化解释DD即试图将某一经由理性确认的所指指派给“法院”--由于文化惯性的原因而告失败,那么,“法院”就成了一个无效的能指,它将面临被拒绝纳入个体原本有序一致的“合理”世界。这样一来,要使得“法院”一词成为共识,并成功地担当文化功能意义上的符号,就不得不向“除魅”的倒退,即抽空它所具有的真实内涵,将某种沉淀于集体无意识的观念表象重新指派给“法院”。
一旦克理斯玛要求被重铸,“人民”一词就会有用武之地。它可以依靠词语本身唤起的想象力量,激发出群氓式的与共感和面对巨大齐一性时的习惯性谦卑;没有什么比作为集体的、抽象的“人民”更能让人心生恐惧、更能让人心甘臣服的了。也没有什么比对共同体的热忱更能让人甘愿放弃理性。一种宗教情感会随着“人民”冉冉而生,支撑起了乌合之众们的正义观。
如此一来,作为一种象征性的权威,“人民”就顺理成章地被用来填充那个空洞的能指DD“法院”,使它重新成为个体可理解、可期盼的有序世界的一部分。这是通过词的神话色彩来构建词的理解意义上的和谐的命名法,或者说,这是一种灌输式的、催眠式的教化与被教化,通过直接触及人的无意识而达到观念上的词与实际意义上的物的暂时妥协。作为妥协的一方DD将法院命名为“人民法院”却视人民如草芥的专制集团DD需要“法院”这样的词,来伪饰枪杆子里的政权,支撑起某种表面上的合法性;而作为妥协的另一方DD保守的芸芸众生们DD需要“人民”这样的词,来以自由为代价卸掉所要承担责任与焦虑,因为在他们眼里,“法”所涉及到的不容商榷的正义观念必须在有限的视域内被展示出来,这种确定性应该由反复的感性体验(让“人民”时刻与“法院”同时出现)来保证、通过较为直观的方式(如图腾、宗教仪式、神话,在“文明”社会则体现为“事迹”)来加以维持。理性的认识和由此带来的感性上的颠覆被断然拒绝了,必须让随处可见的克理斯玛DD人民及其“代表”DD发挥效用。于是,“法院”只能通过这种方式被理解,它要求焦虑在这一词出现的时候立刻得以平抚,即为“法院”找一个能够看得见的“归宿”,不再使它游离于主体的认识之外;另一方面,由于要做到这一点依靠的不是对“法院”的理性认识,所以只有通过某种具有神话色彩的、容易通过感性认识而达到共识的词语来对“法院”进行限定性的修饰,把它归纳进使自我认可的无焦虑的认识疆域中。极权主义所提供的“人民”一词,成功地担当了这项任务。
在实际运用方面,“人民”一词也具有明显的反焦虑特征,它可以通过这样的提问而被认识,即何以“人民法院为人民”(及其类似的宣传语)具有的极大的宣传效力?
倘若使用“法院为人民”这样的句式,在宣传上必定是缺乏说服力的;由于作为主语的“法院”对人来说是一个陌生的词,对它的判定要求的是一个由经验所支持的综合判断,在经验未到之处,人或多或少会抱有怀疑;然而,在“法院”前加上“人民”这样的前缀,即“人民法院为人民”,便可以产生足够的移情效应,它可以使所有产生疑问的人通过自我问答式的解读来消弭困惑。其隐含的逻辑是这样的:【法院站在人民这边吗?DD当然是,不然怎么会叫“人民法院”呢!】
在这种比判断句式更有宣传力度的命名方式的背后,是由催眠者与被催眠者共同默认的倒错逻辑而筑建起的和谐幻象;如果说和谐的幻象必须建立在权力对个体智力上普遍的弱化,那么,这同时也应该归功于个体所惯用的应付焦虑的方向性策略。对于问题的答案,在有限的经验不足产生确切的观念时,原本应该存在的焦虑,都切切实实地被回避掉了。“正义存在吗?”、“法律能代表正义吗?”、“法院能公正地依据法律来判决吗?”……倘若采用“提问(怀疑)-焦虑”的心理去直面这种种未知,将会是异常痛苦的,并且,当看到明显的不正义和不公正现象发生在自己周围时,那种焦虑会更加迅速地吞噬个体原本可以安身立命的所有确定性,此时,语词及其带来的想象力,提供了一种消除焦虑的可行方案;上述问答式的自我解困便应运而生了。
尽管对逻辑的忽视程度令人诧异,但这的确是最可行的一种回避焦虑的心理防御机制。其所遵循的要则是:“想达成你的愿望吗?请别顾合不合理。”在这种心理防御机制的背后,可以明显察觉到一种由传统文化支持的大众神经症,它主导的是在心理需求与外部现实的妥协中所寻求的无焦虑。这类神经症得以盛行,或者说,符合这类神经症的特殊的思维逻辑得以生效,则必须倚赖集体主义教育对个体判断力的羞辱的强化作用所带来的普遍自卑,它使得个体断绝了所有可能通过解决问题的方式来回避焦虑的现实途径,当个体确认本我的满足在外部世界变得不可能,就只能通过梦的方式来寻求解脱。当个体无能力去询问“法院究竟是什么”的时候,他只能让自己沉醉在“人民法院为人民”的荒唐幻想中,以求得一份暂时的安慰。
这样,一种解决困扰的基本形式变得清晰可见。它是这样一种循环:【焦虑产生DD弱化智力、逃避焦虑DD表面上的和谐(压抑、焦虑被转移、神经症症状产生)--焦虑再产生。】
不得不承认,以这样的方式逃避焦虑煎熬,的确达到了实际意义上的效果,起码,一种个体赖以安宁的内心秩序被建立起来了,随之而来的是社会秩序的一系列稳定的表象,这种表象又反过来增强了个体通过此道来处理焦虑的可行性。但毫无疑问的是,这也必须付出极大的代价:它牺牲掉了运用智力-意志力去解决困惑和不安的契机,换来的是则这两方面持久的、普遍的衰弱。
除了“法院”之外,其它那些被“人民”所修饰的词语也具有很显著的特点,如“共和国”、“政府”、“银行”、“公仆”等词。需要注意的是,对这些名词的客观阐释往往并不等价于它们的一般运用,正如绝大部分人都自认为生活在“人民共和国”里但绝不知道何谓“共和国”,仅仅就这些词可能引起的观念表象而言,真正使它们产生作用的,并不是其清晰可见的所指,恰恰相反,它们通常是由于其矛盾性而被接受和被理解,在这里存有的是“一致/独特”、“全体/个体”、“满足/丧失”、“善/恶”、“敌/我”、“本我的欲望/超我的要求”等一系列二元特征。
比如,“共和国(国家)”一词,它的观念表象是这样一种矛盾的产物:一方面它意味着安全、温暖、互助、有序,它是无所不在的父爱;而另一方面又意味着强力、暴戾,它要求奉献与牺牲,它处处限制本我生物性的满足。而“政府”一词,它同时意味着“制定策略扶助人民”和“制定策略侵扰人民”这两种可能性;“银行”意味着价值的保有(货币的实用价值及货币的象征价值)和价值的丧失(通货膨胀时的经济损失及对“一无是处”的自我评价);“公仆”意味着权力带来的秩序和权力带来的压迫。可见,当上述这些词,就其所能在个体头脑中唤起的印象而言,不仅始终是非确定的,而且往往是对立、矛盾的。在这种对立中,焦虑感便挥之不去,因为个体相当明确地意识到,所谓的“国家”、“政府”、“银行”、“公仆”,它今天会展现美好的一面,对你伸出温暖的救助之手,而明天可能就会换一副面孔,让你痛不欲生。惟一能够使这种矛盾性和不确定性转变为一致性和安全感的方式是,去追问什么是“国家”、什么是“政府”、什么是“银行”、什么是“公仆”,即通过理性认识来彻底清理这些词,使词的明确所指浮现出来,当国家行使权力的权限被界定、个体服从权力的理由被阐释,那么“国家”一词才有可能保持词的纯洁性与稳定性,对立两极的矛盾通过彼此商讨、彼此要求、彼此妥协而达到整合,焦虑在此时才有可能消失。一旦上述方式并未被采用,焦虑就始终会伴随词的矛盾性,“国家”、“政府”、“银行”、“公仆”均扮演着天使与恶魔的双重角色,今天对你示好,明天就拿走你的一切。而个体只能在这种无限焦虑中忍受生活。
此时,“人民”一词再次可以发挥它的作用了。在焦虑中,个体通过“人民政府”来强调“政府”一词原有矛盾性的其中一个方面,即强调善意的方面,来试图消解这种矛盾性。面对矛盾,个体完全放弃了去和词的不确定性进行抗争、谈判、讨价还价的可能性,而仅仅是用“人民”这一词所展示的观念的幻觉去弥合矛盾的裂缝,个体不用作任何努力就可以达致了他所想要的无焦虑状况,而权力获得了统治方面的实惠。这种表面上的双赢使得社会的和谐与个体自我的和谐双双获得了现实意义上的完美展现,但焦虑并没有消失,焦虑只是像灰尘一样被扫进旮旯里,在心灵的暗无天日之处慢慢地滋生病菌而已。群体歇斯底里的大爆发是这种“双赢”的最直接的后果。
词二:永远正确/和谐
可见,类似“人民”这样的宣传话语,是一种可以通过个体的心理防御机制而产生普遍的现实效应的政治宣传,在其中,反向作用(reactionformation,或称反向形成)DD作为一种心理防御机制最常见的实际运用,尤为清晰可见。
反向作用是指,人们把自己无意识的情感和想法以较为极端的相反形式表现出来,以抚平焦虑。比如:一个迷恋色情文化的人却热衷于参与反色情运动;对某人的仇恨却以滔滔不绝的赞美之词来掩饰;自卑的人往往表现出强烈的攻击欲。反向作用可以很明显地体现在卫道士们身上,他们用最恶毒的话语对自由主义思想进行诋毁,指责它们败坏道德,这或许可以看作他们对自身所具有的“非人性成分”的一种无意识的抗拒。由于反向作用是一个无意识的过程,所以,无论思维敏锐的学者还是麻木不仁的愚民,都可以深陷其中。弗里德曼在阐述“犹太知识分子何以反对市场”时曾指出,以懂得经商之道而闻名的犹太人中之所以出现了如马克思、马尔库塞、托洛茨基等一大批反对市场的思想家,这与他们犹太人的身份、与当时犹太人被指责为“吸血鬼”的这样一种普遍观点有联系。犹太思想家试图极力摆脱他们这种名声不佳的处境,他们想向别人证明,犹太人绝非无视道德的渣滓,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靠别人的劳动来养活自己。以至于到最后,这些犹太思想家索性扮演起了先知,杜撰“大写的历史”来宣告资本主义的死亡。这同样也可以看作反向作用的体现。
一般认为,反向作用所表现的行为通常流于过火、浮夸、装腔作势,并具有强迫性。它是对焦虑的非理性适应,它歪曲现实,使人格变得刻板僵化。然而,这毕竟有助于个体获得暂时的人格同一性,以达致无焦虑的稳定状态。所以,这也成为“喉舌”在进行思想统治时所遴选的诸多手段中最受青睐的一种心理防御机制,最终体现在宣传话语上的,即:对“永远正确、伟大、光荣的……”与“和谐社会”这类话语的不断重复。它们惟一的作用是,致力于将反向作用的效应扩大化。
大多数人会觉得,像“永远正确的党”之类的宣传话语,已经产生不了任何作用了。一种乐观主义认为,伴随着启蒙的不断深入,已渐渐迎来了偶像的黄昏。更何况,如今的市场经济给人们所规划的行为特征是,人们必须不断地调整自己原有的策略,去配合那只“看不见的手”,只有这样才能在市场上为自己牟取更大份额的利益,在这里,“永远正确”是不可想象的。经济自由主义正是以此开始促动人们的神经,继而则是权利意识的不断觉醒,最终,蒙昧终归会让道于文明。类似“永远正确“这样的极权主义式的宣传话语,只不过是威权政府出于惯性使然罢了,更多的人将会以戏谑的口吻来谈及它,再也没有什么人把它当一回事了。
显然,上述这样的看法忽略了至为关键的一点,即,宣传话语所要影响的并不一定是人的意识,它未必旨在改变人的观念。换句话说,如“永远正确”这样的宣传话语,它并非力图使人们产生一种明确的共识,它决不是诉诸于“说服-被说服”的模式而试图让人们接收“党是永远正确的”这种观点,恰恰相反,它侵入的是人的无意识领域,通过不断地暗示,促成反向作用效应的扩大化,以此来应对焦虑的增长,并把焦虑可能引起的冲突扼杀在萌芽状态之下。
我们可以用一个生活上的例子来诠释这样的过程:一个顾客到小贩之处购物,当他拿起某件物品,仔细端倪之时,他通常会随口问道:“老板,这东西究竟好不好啊?”显然,这是一个愚不可及的问题,因为他必然会得到一个肯定的回答,哪有卖瓜不夸瓜甜的?如果这其中有什么合乎逻辑的地方,那么只能解释为,问题的中心一定不在于“好还是不好”这样一个价值判断,顾客并非试图得到某种咨询,以便衡量商品的价值,而是,顾客想要获得在对“是否购买”这样的问题上存在的犹豫不决所带来的焦虑感的一种平抚。在这里,焦虑伴随对自己的判断的深深不信任而来,“如果买,会不会吃亏了?如果不买,会不会错过了好机会?”此时,倘若有一种来自外部的声音,它是如此铿锵有力,以至于它像真理似的不容人不信,那么,焦虑便会由确定感的增强而得到控制。精明的小贩一定会抓住这个机会,他在说“好”的时候,绝不可能诉诸合乎逻辑的推理,不可能回答“何以好”,因为促动顾客的思辨只会增加他的怀疑;而是,小贩必定会故作姿态,将“好”说成似乎是人尽皆知、不容怀疑的事实,他可以用“绝对”、“一定”等词来加强语气,并不断重复“好”这个发音,声嘶力竭般地扩大它的音域。所有的造势都有助于使顾客明白,没有人会对这个判断产生任何质疑。这样一来,原本存在的焦虑由于外部强烈的暗示而烟消云散了。个体不仅购得了商品,而且附带获得了对商品的有用性的肯定。
上述的例子也许可以说明,个体绝非被动地等待某种信息的灌入。只要有焦虑产生,个体便会不自主地从外界寻求某种暗示,只要这种暗示(通常表现为反向作用,即通过非理性方式对令人焦虑不安之物的反面进行强调)有利于焦虑的缓解。如“永远正确”之类的宣传话语,正是起到了暗示的作用。此类宣传话语通常尾随着焦虑而出现,并根据个体的焦虑、个体对暗示的需求的不断变动而作自我调节。当一种普遍焦虑感被体验为:所谓的执政党的正确、伟大、光荣,在开放社会中民智的不断提升、个体权利意识的不断觉醒的情况下,受到了强烈的质疑,这种质疑及其带来的不满情绪无法通过合理的社会冲突而得到有效的整合,所以,它或是成为现实的痛苦、或是成为驻留在个体无意识领域之中的焦虑,此时,个体对某种暗示具有强烈的需求,这种暗示能够通过“反向作用”来影响个体。无意识非常乐意接收“永远正确的党”之类的观点,当人没有别的途径来改善自己的境遇,也没有别的方式来缓解自己的焦虑,那么,作为一种心理经济策略,相信“永远正确的党”要比在怀疑中忍受焦虑要可取得多。即使在人们的头脑里并没有“永远正确的党”之类的观念,只要焦虑的出现与话语的反向效果形成一种惯有的联系,即“永远正确”只要在怀疑及焦虑出现那一刻的发挥效用,那么,这种宣传话语的目的就达到了,它可以表现在个体不为人知的自言自语中:
【党是正确的吗?我看不像,不过大家都说它好,也许我只不过杞人忧天,算了,不管这个烦恼的问题了。】
上述话语可以进一步理解为:
【党是正确的吗?我看不像,但我怎么能忍受一个如此错误百出而又不协调的世界呢?我怎么能够忍受一个正义泯灭、卑劣却处处得势的世界呢?这对我打击太大了,我受不了,所以,就姑且相信党是永远正确的吧。别让我承担焦虑的折磨就可以了。】
每一次怀疑均是一次痛苦,每一个“永远正确”均是一剂麻醉药,暂时的安慰起码使人有借口逃脱对问题的深究。如果要给这样的宣传话语一个恰当的名称,称其为“精神毒品”并不过分。它给予个体的是即时的快慰,免除了人的内向性思考与由此带来的焦虑。它通过对个体的无意识的低声轻吟来勒索理性:尽管这些都是连篇鬼话,但为了你的无焦虑的幸福感,你还是相信它为好。
与此相同,“和谐”一词被频繁地用作官方宣传,它也是对处于剧烈变革时期的社会中随处可见的不和谐之音的反向强调。这种不和谐之音随处可见:受教育时所接受的利他主义观与现实生活中的丛林法则的不和谐;被承诺的道德理想国与现实生活中虚伪、阴险、狡诈之人往往左右逢源的不和谐;心目中所谓的泱泱中华的灿烂文化与在和西学的比较中相形见拙的不和谐;最重要的则是,各个处于分化状态的群体的实实在在的利益冲突。“和谐”一语,与其说是将某种行政目的告知于民,倒不如说是通过“反向作用”来对矛盾不断否定。它并不涉及任何对社会矛盾的分析,也不致力运用有效的方式化解矛盾,换句话说,它从来不关心“如何和谐”这样的问题,相反,它的惟一目的是利用喉舌强大的宣传工事,将人们心底隐隐约约感到的不和谐感彻底抹去。【你感到不和谐吗?放心,我们(党/圣人)说了,要努力构建和谐社会,所以你不用焦虑。】
起到“反向作用”效果的宣传话语,它犹如一块补丁,根据当时社会的不安定因素的变化而改变自身符号,来捂牢所有社会焦虑及可能带来的冲突。当党的所谓“先进性”受到普遍怀疑,就会有“保持先进性”这样的宣传话语;当党魁们被认为是一群只顾自己利益的自私之辈时,就会有“代表”之说;当既得利益阶层在搜刮民膏时过于贪得无厌而遭到普遍的不信任时,就会有“荣耻观”的提法。(在这里,荣耻观并非仅仅是一般的道德驯化,它包含这样一层意思:请相信我们(党/圣人)是有荣耻观的,因为我们在不停地宣传荣耻观。)编纂此类宣传话语的喉舌们远比一般人更为敏感地意识到诸种可能带来冲突的社会问题。它们所要做的,就是通过铺天盖地、无孔不入的符号灌输来使个体在面临焦虑时更为倾向于利用反向作用来自我安抚。无论此类话语本身怎样变化(“人民”、“永远正确”、“和谐”、“先进性“、“盛世”……),它们从来都不作为一般意义上的词用来交流,而是一种单向度的、有条理的符号发布与信息控制,其中每一个词都应对一定处境下的普遍的社会焦虑,它们旨在让面对焦虑感到无所适从的人们经由非理性的方式(反向作用)寻得当下的慰藉,在此,焦虑得到了遏制(或者,如下文所示的那样,只能说通过神经症症状而被“转移”),只有这样才能杜绝一切焦虑所引起的改变现状的愿望的产生,某种和谐的假相便应运而生。
词三:统一/屠杀
心理防御机制可以被看作一个“压抑”的过程。而伴随压抑的,决不可能是真正的和谐。在这方面,个体和社会是极为相似的。强迫性神经症和癔症病人,均是通过某种行为来进行替代性满足,以作为“被压抑之物”的补偿;而就一个社会而言,在压抑普遍存在的情况下,这种替代性满足完全可能被引导为某种集体意识,并通过进一步的集体行为来强化,最终形成一种大众神经官能症。这种神经官能症是一种“无个性的强迫症”,症状再也不是从个体各不相同的境遇中产生,而是从某种被赋予高尚感,且更为符合原始自恋心态的共同意识中产生。无论其是否被冠以意识形态之美名,或是否由多么雄辩的说词来证明其正当性,都可以称作“症状”。
在《抑制、症状与焦虑》一文中,弗洛伊德探讨了由焦虑和压抑产生的后果,他写道:【焦虑促使压抑启动。压抑等同于逃避的企图,自我把它的前意识的贯注从即将受到压抑的本能代表那里撇下来,并且把该贯注用于释放不快乐(焦虑)这个目的。……症状是一种以已经束之高阁的本能满足的标记和一种替代物,它是压抑过程的一种结果。】如果焦虑、压抑和某种神经症症状之间有某种因果联系的话,那么,在一个焦虑被普遍意识到,而压抑过程显得如此劳师动众的社会里,是否存在着某种症状,它有助于焦虑的释放与压抑的完全成功?这样的症状的特点又是什么?【在强迫性神经症中,如果症状形成成功地把禁律与满足结合起来,进而使最初仅作为一种防御命令或禁律的东西也获得了满足的意义,那么,症状形成便取得了胜利,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它将常常采用最有独创性的联想道路。】
弗洛伊德所强调的“禁律”与“满足”的结合,即,使这两种原本不相调和的事物在某种症状中成为一体,可以在当下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中体现。在这里,“禁律”和“满足”均非常明显。最基本的禁律也许可以表达为《圣经》的上:【要爱你的邻人如爱自己。】它包含着“禁止侵犯他人”这样一条文明社会的规训。但倘若出现这样的情况,即,当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凝聚社会成员的道德力量处于失范状态,借霍布斯的话来形容,“人对人就像狼对狼一样”,“是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此时,“爱你的邻人”几乎就成了不可能做到的事情。要使这样的禁律继续生效,最好的办法是把它结合入某种神经症症状之中,使禁律本身具有“满足”的功能。而所谓的满足,如弗洛伊德所言:【心理活动的最终目的可视为一种趋乐避苦的努力,而从经济的观点来看,则表现为将心理器官中所保存的兴奋量(或刺激量)加以分配,不使它们积蓄起来而引起痛苦。】满足表现为将经过压抑的焦虑情绪以适当的方式向外投射,使得焦虑(作为一种引起不快的刺激)不至于因压抑而驻留在心理器官中造成不适。在神经症状态中,满足即宣泄。倘若仔细观察的话,可以在那些高喊着民族主义口号的群氓的脸上明显察觉到某种与性亢奋相类似的表情特征。对他们来说,满足感随着情绪的肆意发泄而获得。
如【中日必有一战】这样的宣言,是“禁律”与“满足”的最完美结合。禁律依靠对“你/我(日/中)”区分的强调来定义“邻人”,即来决定谁应当被爱。它提供了一个清晰可见的分野,使得爱的对象与恨的对象成为可以轻易获得的具体目标。当个体在社会交往中对他者的不信任感与疏离感日渐加深时,谁究竟应该被爱,谁究竟应该被恨,这成了一个很大的疑问;每一个“他者”均带着一副面具装腔作势般与人周旋。政治精英是说谎机器;官僚们只想着劳尽好处;油头粉面的学者们总是用高深莫测术语来为既得利益群体辩护。在这个社会中,所有本被认为是善的、美好的东西可能在顷刻间化为一团幻影,留下的只是奸人的偷笑。这种幻灭感不断地侵蚀着每一个人,如此一来,“爱你的邻人”这样的禁律再也无力维持下去了,在每个人的心里,邻人只是个会变脸的恶魔,一个潜在的骗子。此时,倘若向个体提供一个可以仇恨的对象,即,恨意被约束到特定对象身上,那么禁律仍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得以维持。一个如此明确的可恨对象,就能够使个体在是否遵从禁律的巨大怀疑中解脱出来。再也不用提防“邻人”了,敌我关系已经明确,恨的对象给予了所有被怀疑的邻人以反衬,原来遭憎恨的“同胞”在此时突然变得如此可爱了。
民族主义情绪中的一些被呼喊得最为响亮的口号,均可以被认为是“说”出了禁律。如【日本人是畜生】这样的话语,其更为直接的表达应为:【我必须遵从禁律,爱我的邻人(中国人),因为他们与日本人不同(不是畜生)】。这样的禁律对维持社会凝聚力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它的有效性是靠通过承诺快感换来的。快感来自于经受压抑的焦虑的释放,焦虑通过歇斯底里般的呐喊而消耗在对纯粹正义的幻觉中,快感在此时被捕获,个体在实践禁律的同时也获得了生理意义上的满足。当然,这样一来的话,遵从禁律就等于完全抛弃个人道德主体的身份,它根本上无助于真正的道德建设。原本摇摇欲坠的禁律只是由于混杂了快感体验,才变得容易让人接受。它必然要不停地讨好本我生物性需求以换得自身的维持,它与“头顶上的星空”彻底划清了界限。
时下被称为民族主义情绪的,很大程度上可以都被归结为由普遍存在的焦虑和压抑而产生的神经官能症,在其中,禁律正是以这种强迫症的形式,给人一种“民族团结”的假相。由于禁律在民族主义情绪中的确得到了加强,原本在社会个体之间愈演愈烈的摩擦似乎显得微不足道了,同仇敌忾的民族一体感让人把矛盾抛到了脑后,人们突然发现,不与“邻人”起争执却又能满足自我,这并非不可能的事。禁律演绎得如此惟妙惟肖,以至于头脑简单的人会大呼“民族主义能救中国”,殊不知,这样的禁律只是症状表面化了的特征,它必然以施虐欲、破坏欲的彻底释放为前提。在民族主义情绪中体现的一系列心理过程,就如一个被上司辱骂却不敢作声的小职员,回到家中对着妻子儿女发泄不满。尽管总是以张牙舞爪的形象出现,但在这里看不到任何对个体权利的伸张或对“主人道德”的渴求。某种不愿面对现实焦虑的逃避的类型可以在其中被发现,它披上了“爱国主义”的羊皮,使个体更容易以自己的懦弱为荣。
在这种大众神经症形成的过程中,宣传话语,即舆论的控制是至为关键的一点。围绕着“统一”和“屠杀”的一系列有利于民族主义情绪激增的宣传话语,通常均是以“知识”的面貌出现(诸如“某年某月发生了南京大屠杀”、“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等等),但它们的真正作用则是巫术式的。列维-斯特劳斯曾经分析过萨满巫术的治疗效应,这种巫术通过萨满法师口中的念念有词和形体上的特殊动作来治疗疾病。他说道:【细菌与病人的关系,在病人的意识中是外来的,这是因果关系;而魔怪与疾病的关系在病人的意识中却是内在的:这都是象征和象征物之间的一种关系,或者说,是能指与所指之间的一种关系。萨满向病妇提供一种语言,凡是没有表达出来的,或用其他方式无法表达的各种心理状态,都可以借助这种语言立即表达出来。正是由于改用了这种语言表达,使生理过程释放出来,也就是说,使病妇所经受的这种过程朝着有利的方向重新组合。】现在,焦虑正如某种折磨人的病痛,它无法被认识和表达,所以需要巫术语言,并以知识的形式被授予个体。【冲突和阻力的解决都不是由于病妇逐渐获得的知识,而是由于这种知识能够使冲突在一种特定的经验过程中,按一定次序并在一个层面上具体化,从而使冲突自由地发展并获得解决。】制造民族主义情绪的宣传话语,类似萨满式心理-生理治疗的现代版本,它力促每个被动接受的个体去自发地形成弗洛伊德所指的“独创性的联想道路”。焦点并不在于任何政治现实主义的考量,而在于,每个社会成员的想象力必须被调动起来以形成释放焦虑的通道(即话题本身)。宣传话语必须做到的,就是要千方百计使焦虑具体化、可视化,使焦虑化解成可以被合理解释的某种情感的一部分DD“如果你感到焦虑,请责怪台独分子;如果你感到焦虑,请痛骂日本鬼子。”这样的情感只要傍着意识形态的美名便可肆意挥洒以制造快感。由于宣传话语具有相当强大的感染力,它可以不断地提供话题,让“联想道路”变得随处可及,以便就时就地给焦虑赋形,指定焦虑的流向,让不甘处于压抑状态下的焦虑情感在某个话题的可笑的讨论中得到发散与消耗。当然,这一切必须回避产生焦虑的任何实质困扰与真实缘由,也正是因此,神经官能症式的“禁律”与“快感”的结合便成了唯一后果。
一旦宣传话语的目标已经确定,剩下的不过就是手段问题。如何使得诸如“台独不得人心”或“日本亡我之心不死”之类的观念能够成为普遍共识,或者说,如何使症状作为对宣传信息的反馈而被确定下来,如何使“联想道路”成为个体处理焦虑时的第一选择,这是宣传话语所努力的方向。传播学和舆论心理学开始展现它们的威力,在专制主义和现代技术的通力合作下,一切都不过只是工程和计划。拿新闻为例:一段讯息在成为新闻条目之前会经过多种处理步骤,比如:对讯息的进行切割、润色;对某些细节着重渲染;采用能引导人使其更为情绪化的修辞;斟酌每个语词的力度与讯息发布在时间上的密度;发布时略去声音的总体背景与环境的介绍;切断来自相反意见的声音源。总之,它不再采用高强度、千篇一律的教化,而总是貌似以“他人意见”的代言者(诸如,某某说,某国怎么怎么;某某认为,某人怎么怎么)的公正形象出现,它可以通过普通人对于“报道即事实”的权威的全然信赖,来进行思维和情绪的导向。舆论控制再也不是简单的重复和断言,宣传话语虽然也显现出了对个体自主思想的大规模围剿的态势,不过围剿的目的不再是使个体投降,而是将他驱赶进一条刻意留下的小径;围剿者的目的再也不是仅仅为了控制个体自主选择的可能性,而是让个体陶醉在某种自主选择的假相中。
在这种类似宣泄疗法的社会宣传中,除了一些明显带有猥亵性质的、用来满足“口欲”的语词外,还有一些语词,在脱离其本意的情况下,仍具有着相当积极的意义。弗洛伊德曾谈到:【语词观念的投注并不是压抑行为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代表企图走向痊愈的第一个努力。这些企图和努力在精神分裂症的治疗过程中是十分明显的,它们的指向是要重新获得失去的对象。情形很可能是这样:为了要实现这一目标,它们通向对象的道路就必须是经由那从属于该对象的语词;然而这样一来它们也就不得不在本该满足于具体事物的地方使自己满足于语词。】倘若如弗洛伊德所言,语词观念是一种向精神分裂症之治愈的无意识的努力,那么,就很容易解释类似“统一”和“屠杀”之类的语词其本身何以意味着满足。所谓的“祖国要统一”的口号无非是个体回归自然本真状态的一种尝试性的呼唤,其目的则是“自我要统一”;这可能是缘于现代性所带来了巨大不安和非平衡,以及社会多元化引起的大量焦虑及异类恐惧症,使得“自我统一”变成亟待解决的问题。很不幸的是,一旦戴上了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的面具,颇有几分向纳粹党看齐的味道。此外,“屠杀”意味着“被侮辱的和被损害的”人们的日渐觉醒。作为一种隐喻,“屠杀”的主词与宾词均不重要,它只是依靠唤起想像力,来试图将某种原本由极权政治的高压所造成的创伤意识的割裂重新接合起来,这是个体自我复原的一次尝试;一旦条件允许,那些“被侮辱的和被损害的”人们将会像罗马尼亚人撕碎齐奥塞斯库那样找到正确的复仇对象。
时下的宣传话语必须同时以这两种姿态出现:一方面是不断的压抑,每隔一段时间就会针对社会的普遍焦虑来设计宣传口号,由传统的灌输方式筑起心理防御的城墙;另一方面,由于压抑产生的副作用可能会导致的种种社会悲剧(最极端的,如因个人不幸而制造恐怖事件向社会报复),所以必须由另一些宣传话语,负责对焦虑的疏导和转移。这两种姿态的宣传缺一不可,没有“压抑”,就无法“移情”;没有“移情”,“压抑”将会使人不堪忍受。通过这种“移情大法”,形成了一种被当下文化认为是“值得赞赏的价值取向”,且美其名曰“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显然,这并不是诸如“政治热情”之类的里比多在文化层面上的升华。精神分析学家西弗尔伯格曾说道:【移情可以看作是人对现实的深刻反叛和以不成熟方式进行的顽强抵抗之持久的纪念碑。】移情性神经症始终在“不得不说”和“说不得”之间摇摆不定,并缺乏勇气面对现实。阿德勒也认为:【对丧失勇气的人来说,神经症和精神病是一种表达方法。】
在精神分析学看来,只有回到焦虑的源头,去发现和认识被压抑的无意识情感,才能使神经症患者走向康复。随着替代性满足的消失,一个健全的、强大的“自我”才有能力驱走神经症,并成功地统御人格。这就要求个体乃至整个民族具备勇气去直面焦虑、认识焦虑和接受焦虑,不把它当作一种病态心理的产物,而是当作外部环境赋予的一次改善生活的契机。这里将会迎面遇到传统价值观的抗拒,即“人的无焦虑状态位列诸价值之首”。这样一种普遍观点时至今日仍无可动摇:谁带来了纷争,谁就是恶魔;谁带来了稳定,谁就万万岁。而在这种主导观念下,自由主义式的政治实践是无法想像的,因为任何程度上的“试错”都意味要以积极的态度聆听反对意见,并甘愿去不断修正那被神化了的旧有秩序和体系。不安定感所引发的焦虑必然会与“试错”带来的社会进步将会同时存在。要么在“总统靠得住吗?”这样的焦虑中忍受生活,要么接受极权者“永远正确”的统治。前者总是可能带来无尽的烦恼和折磨,人们不得不殚精竭虑地致力于对统治者权限的不断修订,既给予必要的权力以维护国家安定,又使得专制越来越变得不可能;后者则是相反,人们将统治者奉为神明,甚至任凭他作威作福,作为回报,统治者必须许诺“无焦虑的幸福生活”。作一个对比就可以发现,在自由社会中个体所采取的政治参与是以“把焦虑承担下来”作为前提的;制度鼓励人们习惯于表达或接受“你不对!”这样的话语,来自各方的多重意见往往把人弄得焦灼不堪,最后总是在熙熙攘攘的争论不断与互相斥责中达成妥协;而在极权社会中,则是把任何程度的焦虑都当作洪水猛兽,为此,所有的政治活动不过是“合理化”的过程,制度拉开神话的帷幕,并为人的主观幸福感而编织了各种符号,使它成为了所有不愿面对现实及其必然带来的焦虑的人们的最终避难所--“既然你不能改变现实,那就改变你的想法”。
我们也许很难对某种文化在应付焦虑时所采取的惯有态度进行指责,尽管在我们这个时代看来,它是如此不如人意。从科学的角度来看,在人类演化过程中,神经系统自行发展了一套极为可行的防御措施,比如,一些人在听到噩耗时会昏厥,这可以看作是神经系统为保护有机体而采用强制与外界隔离的措施。换句话说,“麻木不仁”DD通常被用来形容典型的中国人DD也有它的积极作用,甚至可以说,这是某种生存优势。这同人类的神经症状态相似。而作为文明衍生物的宗教,它显然是一种神经症,它的作用之一,便是提供某种冠冕堂皇的说法,使人类“麻木不仁”到以至于忘却痛苦而继续生存下去。即使被认为是由人类理性所主导的文化过程,在精神分析学家眼里,也不过是一种很特殊的神经症罢了。展望一下我们这个焦虑的时代,有着两种明显的现象,一是大量的具有反焦虑特征的文化产物,像某种失了控的程序,疯狂粗暴地侵凌着孱弱的个体,每个人仿佛都被浸泡在由符号组成的话语世界,由冰冷无味的泛泛说词寻得里比多贯注的可能途径;二是宗教的逐渐深入人心。如果说,神经症无法避免,那么,主导非暴力的宗教远比集体歇斯底里更为可取。而如今的官方宣传话语所带有的强烈的蒙昧色彩及其所同时引起的弱智化、犬儒化倾向,以及一系列过于敏感的国家主义与民族主义情结,都易于把神经症引向集体大爆发。而灾难从来不是某个“伟人”的杰作,却是千千万万个卑劣灵魂的肆意癫狂。一旦习惯于把语词的神话属性当作精神避难所,那么,文明的倒退也只不过刹那之间。
曳航之舟07年1月
作者:曳航之舟 回复日期:2007-2-6 13:33:40 自己顶一下
作者:曳航之舟 回复日期:2007-2-6 18:58:32 没人看么,自己再顶。。。
作者:碧云包租公 回复日期:2007-2-6 19:48:55 哈哈,不错的文章,顶你一个
作者:巴头陀 回复日期:2007-2-6 22:11:18 在精神分析学看来,只有回到焦虑的源头,去发现和认识被压抑的无意识情感,才能使神经症患者走向康复。随着替代性满足的消失,一个健全的、强大的“自我”才有能力驱走神经症,并成功地统御人格。
—————————————-
不敢苟同
这至少不是拉康学派的观点
作者:涛涛不倔 回复日期:2007-2-6 22:30:39 看起吃力,简单最好
作者:刘沙沙 回复日期:2007-2-10 3:27:02 好文章
作者:浮点运算器 回复日期:2007-2-10 08:16:03 向你学习
作者:曳航之舟 回复日期:2007-2-10 20:56:43 顶上去
作者:dzb777 回复日期:2007-2-10 22:15:09 好文
作者:妙德 回复日期:2007-2-10 22:26:10 好文章,可惜看的人少,看懂的更少,楼主若可以把文字转化为更浅显的话语,则学生们学习起来更容易理解一些.
作者:衔杯袒腹 回复日期:2007-2-11 01:38:48 好文章
作者:musia 回复日期:2007-2-12 9:14:11 侵髑吆凸选
作者:musia 回复日期:2007-2-12 14:37:21 仔看完了,佩服侵鳎
可惜很少有人谩
作者:野航 回复日期:2007-2-15 23:13:47 拜读了阁下的文章,佩服得五体投地。看来阁下在精神分析学上的修养,在我之上。
“只有回到焦虑的源头,去发现和认识被压抑的无意识情感,才能使神经症患者走向康复。随着替代性满足的消失,一个健全的、强大的“自我”才有能力驱走神经症,并成功地统御人格。”我觉得,这只是迈出了最基本的一步。在替代性满足的消失与成功地统御人格之间,还有一个重要环节,就是创造力,(或容格所说的寻找霍尔默斯)没有这个环节,替代性满足的消失并不能必然地迈向成功地统御人格,而是陷入精神分裂症。
我还要再细读一下。
我可以将阁下的文章拿到聚会中去讨论吗?
作者:liuge7712 回复日期:2007-2-16 1:22:19 好文.顶
作者:伏灵 回复日期:2007-2-16 10:35:50 好文
作者:野航 回复日期:2007-2-16 22:51:06 与楼主商榷几个问题。
1“反向作用是指,人们把自己无意识的情感和想法以较为极端的相反形式表现出来,以抚平焦虑。”
反向作用可以共时性到表现为把自己无意识的情感和想法以较为极端的相反形式表现出来,也可以历时性地表现为被压抑的无意识因素终于颠覆了意识而成为人格的主导因素。
2【要爱你的邻人如爱自己。】在中国文化中,这一条不是禁律。故国人对日本人的恨不应附会为夹杂着说出禁律的快感。很大程度上,反日情绪是被煽动起来的,目的是为公众导出无意识的愤怒情绪,让其变为可言说有目标之物,以缝合社会自身不可克服的分裂倾向。美国新保守主义将别国妖魔化,试图用恐怖来增进国民之团结与道德,也是这种企图。
3[这样一种普遍观点时至今日仍无可动摇:谁带来了纷争,谁就是恶魔;谁带来了稳定,谁就万万岁。而在这种主导观念下,自由主义式的政治实践是无法想像的,因为任何程度上的“试错”都意味要以积极的态度聆听反对意见,并甘愿去不断修正那被神化了的旧有秩序和体系]。
纷争的自由主义式的政治实践对于西方的意识/无意识结构而言是顺理成章的,因为外向的,多权制衡文化性格必然产生纷争的自由主义。而对于内向的中国文化品格而言,不安带来的不是不同人群间健康的的相互竞争,而是失序,就象台湾所发生的那样。人类在历史关头的选择通常是两难的,为了避免巴尔干化,中国人选择了被专制“劫持”,很难判断那种选择危害更小。能在焦虑中忍受生活的人是少数人格特别强大的人。当然,把这个问题摆在意识面前是有好处的。
4“如果说,神经症无法避免,那么,主导非暴力的宗教远比集体歇斯底里更为可取。”
用宗教神经症代替集体歇斯底里,这药风险也很大。不如发起一场精神分析的思想运动,去提倡随时注视自己的神经症。
作者:闲言不要讲 回复日期:2007-2-16 23:58:42 这样的写法,思维方式,表现方式有建设性.赞一个!
作者:欲海漱石生 回复日期:2007-2-17 0:06:45 十几年前,有个在西南政法学院念书的朋友Z跟俺说。
有一回,有个外教S跟俺朋友Z一起逛街,一不小心逛到一个法院门口。
S问:这个招牌写的是什么?
Z:XX区人民法院。
S问:为什么要加人民二字?
Z:有什么不妥吗?
S;没有,只是纳粹当年的法庭也叫人民法庭,很可怕,所以还是不用好。
作者:曳航之舟 回复日期:2007-2-17 01:18:17 回野航兄:
非常感谢你的认真阅读和回复,对你提出的几点我也随便谈一下
对于反向作用的共文章来源于互联网
有些孩子在放学回家后,常常对父母说“累得不想动了”。这里所说的“累”是孩子在紧张学习之后产生的一种疲劳感,而这种疲劳有的是属于生理性疲劳,有的则属于心理上的疲劳。 生理性疲劳一般是由于生理上的超负荷而引起的。不过,由于孩子们精力旺盛,能在短暂的休息后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