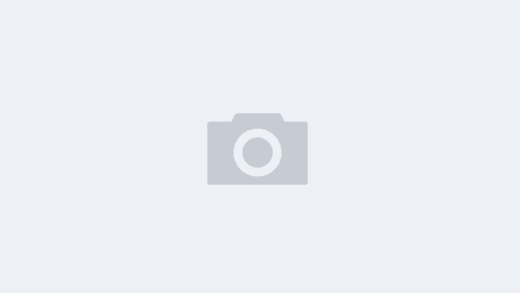不想过年
春节正在向13亿中国人走来,34亿人次正在向春节涌去。
什么都无法阻挡我们回家、回乡的步伐,除了——我们恐归的内心。
在功利的时代,中国人对生活的焦虑在过年时分集中爆发——不成功怎么衣锦还乡?怕催婚,怕被问工资,怕送礼……“过年9怕”在网络引爆了关于过年的集体恐慌。
当春节的团圆意义淡化,家庭成员价值观冲突,越来越多的“恐归族”想说:恐归,并非不想过年,“不归”也许是另一种过年方式,节日生活最重要的是快乐。
一过年,好青年就变成了问题青年。小众的“恐归”族,在我们的专题里成为主角,他们有他们的无可奈何、理直气壮和情有可原。我们盘点了中国人对18种中西节日的好恶,总结了不能过年的10种职业,采访了7类不同滋味的过年体验,调查了国人印象最深刻的各种过年经历。
让我们彼此包容、理解,回归节日的本来意义,祝大家春节——快乐!
“恐归族”的价值宣言
马上逃离!
文/金雯
春节是农耕文化的产物,在消费社会被“物化”,淡薄的年味之外,亲情的功利让人失望,连团圆的意义都在淡化。辛苦一年之后,“恐归族”的心声是:不想过年。
30年前那些逗乐我们的相声段子已经不再好笑;除了在微博上被吐槽,春节联欢晚会已经乏善可陈;大鱼大肉、糖果零食都不太符合现在的健康标准;大扫除是没必要的,日常清洁已经让家里足够干净……过年可以做的那些事情都在逐渐失去意义。
过年必须做的那些事又令人烦恼。2013年春运人数超过34亿人次,每年几十亿人口的大腾挪成为一个基本无解的社会问题。年货送来送去,领导、朋友、长辈,打点各方关系,联络多方感情,过年比上班还累。年前的突击加班常常让人对假期产生幻灭感:焦头烂额地忙完所有的工作,难道就为了过年那几天吃得脑满肠肥,对着电视发呆吗?
我们感慨年味淡薄,其实是人情淡了。但人类社会就是在由熟人社会向契约社会前进。我们有了更多的自我,不再依靠单一的价值标准来要求自己、评判别人,我们对于幸福的定义不再趋同。在不想过年的呼声中,十分具有代表性的理由是:为什么要按照别人的意愿来过年,我们只需要一个属于自己的舒心假期。
过年的那点“乡愁”也不过是脑补后的结果。
春节起源于殷商时期的祭神、祭祖。西周之后,过年加入了农业庆祝的活动。到汉朝形成了新春的礼仪。过年是绵延整个中华文明的传统。1928年,国民政府曾经试图废除春节,折腾了几年后自动放弃。“文革”期间的“革命化春节”也响应寥寥。民间对于风俗习惯,特别是对好吃好喝的节日的眷恋是强大的,过年,在中国人的生活中一直很难被撼动。但是,从20世纪初开始,个体便已经开始精神上逃离这种传统。
鲁迅在《祝福》描摹了过年的场景,宣告了自己的逃离,《祝福》中的“我”是这样一个人:一个读了点书、见了外面世界的小知识分子,他不再依靠惯性来生存,开始冷静审视这个“过年”的旧世界,并在其中看到残酷。
《祝福》中鲁镇旧历年底在天空中都能显出即将过年的气象,所有人都在忙着年终大典“祝福”,杀鸡宰鹅,买猪肉。但洗涮是女人们的事情,仪式是四叔这样的家长的事情。“我”这个无关的闲人,回到故乡鲁镇,却急着想要离开。那是一个充满了“寒暄”的世界,总是话不投机,有些你怜悯的可怜人,而你帮不了他们;有些势利心狠的人,你厌恶又不免有些交道。若干年后回顾起来,故乡已经很远了,过年便只是记忆中灰白色的天空,远近的鞭炮声和弥漫于空气中幽微的火药味。
我们会在某一瞬间怀念四世同堂的时代,全家欢天喜地过春节。但在理智层面,我们都明白,那不过是一个幻觉而已。家庭人口越多,关系就越复杂,大家庭内部从不缺勾心斗角,也像一个小江湖。一些据说饱尝了都市孤独症的人怀念记忆中的春节:现在想来跟兄弟抢一块糖都是开心的。他们已全然忘记当初没有吃到那块糖的愤懑与屈辱。在一些充满乡愁的脑海中,过去总是蒙着一块玫瑰色的面纱——那其实是脑补的结果。
现实没有给乡愁留下空间,城市化推平了记忆中的故乡,在“千城一面”之间,我们的家乡都是趋同的,几年之间迅速崛起的市镇只跟地产、政绩相关,与出生或生活于此的人没有多少关系,为了活得好一点,他们甚至都不能留在自己家乡。
对于世界工厂流水线上的90后来说,公益短片中那些千里走单骑,冒着风雪骑摩托回家的情感是陌生的,那是他们父辈的过年经验。对他们来说,过年开心的不一定是回乡,而是拿了工资去买一个新款智能手机。QQ上认识的好友比儿时的玩伴亲密得多。故乡是丑陋的,他们对于中国乡村的凋敝体会至深,那是留守儿童时期的切身经历,在父辈打工赚来的二层小楼中,只有未粉刷的墙壁、祖父母力不从心的照料。
过年是代际矛盾的爆发期,两代人都深深地被那个无法实现的“成功”所折磨。
虽然这个国家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与世界的同步,年轻的一代能够与全世界同龄人同步在苹果店排队抢购最新一代的iPhone了。但是上一代人还在另外一个时空:依然相信电视上所说的一切;对他们来说,网络最大作用就是偷菜以及可以连续看完三十多集的“婆媳大战”连续剧;他们或许是广场舞大妈中的一员,或许是买金大妈中的一个。他们早早就已经放弃自己,而把全部的希望放在儿女身上:只要儿女好,他们便一切都好。在一个飞速发展的时代,他们也迅速放弃了自己的话语权:我搞不懂了。家长权威开始丧失,长辈对于家庭的凝聚力也越来越弱了。
对很多中国家长,特别是中国父亲来说,亲子沟通是一件困难而麻烦的事情。养育孩子的那几年恰好是事业上升的关键阶段,与同事在一起的时间超过陪孩子的时间,孩子的叛逆期又恰逢中年危机,出轨闹离婚各种焦头烂额。在2012 年,中国的离婚率增幅就已经超过了结婚率增幅,连续8年攀升。
向孩子解释成年世界的各种困境实在太困难了,也太耗费时间了。情感上的亏欠很容易用礼物的方式来弥补。一个芭比娃娃、一套乐高玩具、一个包、一辆车、一套房……亲子关系变成了礼物模式。但是,养育一个孩子并不是驯养一个小动物,给它粮食,它就会向你摇尾巴。情感互动是一种经年累月练习的结果,不是你某天突然想修复时,就可以让对方按照指令回到原位。情感上的空洞会一直横亘在彼此之间,过年也无法让大家在一起假扮亲热。
年轻的一代多数是精致的利己主义分子,从小便享有家中最好的一切。花着父母的辛苦钱念完了大学,第一份工作的工资还不足以支付房租,在一个“拼爹”时代,当他们工作受挫时,还不时会暗暗抱怨:为什么自己不是富二代、官二代。
父母与孩子照例是最亲密的亲人,却有着最无法沟通的价值观,他们都被这个时代的功利主义牵动着,无法自省,也无法以恰当的方式爱人。父母依然还在付出,但是付出得越多,希望在儿女身上得到的回报就越多——不是希望儿女返还自己什么,只是希望在儿女身上兑现自己无法取得的现世成功。但是身为儿女,却并不是个个都能出人头地,那些厌恶过年的大多数无法面对自己现世奋斗的“失败”,败于过年聚会的各种“晒”:晒年终奖、晒过节福利、晒年会上的抽奖……三十而立没能立起来,四十不惑依然困惑,难以担当那些人生的责任;他们没能成为一个好的榜样,提供一个世俗层面的成功样本。
过年是农村包围城市,品味、学识、腔调……都市优越感在过年期间全面沦陷。
人是依靠优越感存活的动物。在北上广深,你可以看伍迪·艾伦的电影、用海淘购买一千美元的鞋子,然后假装生活在纽约。单身无孩,月月月光,除了生病时偶尔会觉得有点寂寞,总体依然觉得自己人生很牛,觉得自己是超越了琐碎生活的那群幸运儿。因为你就是在琐碎中长大的,上有老下有小,空间局促,没有隐私;从物质匮乏时期过来的父母,小心地计算着每月的开支,为节省了10块钱而雀跃不已。熟人社会有各种人情世故,斤斤计较,你是如此厌恶,大学毕业后便义无反顾地逃往大城市,以为远离了是非与琐碎。
但是年龄渐长,你会发现,自己还是难以逃脱被那些在你看来井底之蛙的眼界评判。春节其实是一个“成功人士表彰大会”,中国式幸福是如此单一而残酷,就是有票子有房子有车子有儿子。那些没有比较优势的人讪讪退回到亲情环节,长辈发了压岁钱,晚辈送完脑白金,大家开始看春晚包饺子。晚会歌手在唱“常回家看看”。你在心里却暗暗下决心:明年混不出个样子来就不回家过年了。所以,每年春节都会有那么几个缺席者,他们是家人口中隐晦的存在,“没回没回”,最后一声低得几乎听不到。
在家乡不要试图去推销那套雅痞的观念,喝什么红酒、穿什么质地的套头衫。在强大的现实主义逻辑之中,你就是一个不会过日子的废柴。由品味构成的大城市优越感可以瞬间被洞穿:言必称纽约,却一次没有去过纽约,其实只够钱去次泰国;每个月仍在还15万的奔驰smart车贷;过完年,房东就要涨房租,心里一直在挣扎要不要搬离电梯公寓;年终奖很少,过年这一次回家就全花光了;信用卡已经有了三笔分期,难道还要继续第四笔分期付款吗?
在家乡湿冷的冬天,凹造型穿着单薄的羊绒大衣冻得瑟瑟发抖,然后,那个微胖的妈递给你一件羽绒服,你挣扎了一下还是穿上了。你会发现,跑了很久,以为自己已经远离了你所否定和逃离的一切现实,但是,回家过年,一切都被打回原形。只是温暖和安全感是很受用的,虽然它们总是与现实的无聊、琐碎一起出现。
“不归”是另一种过年方式
重要的是快乐,不是过年
文/谭山山
图—阿灿/新周刊
尽管不时出现“回家过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陋习”(罗永浩语)这样的激烈反对声音,年还是要过的。而社会在变,生活在变,人也在变,相应的,过年的方式也在变。
在写于1935年的《记元旦》一文中,林语堂描述了自己从拒绝旧历新年到败给传统习俗的心路历程。他先是坚决地表示,“我的科学意识叫我不照旧历过新年,而我也答应我不会”,然而,从仆人送来一碗腊八粥开始,他已经感觉到旧历新年的到来。而让他一发不可收地勾起对旧历新年美好记忆的,是一盆从福建老家送来的水仙花。
“我不觉回忆到我的童年。当我接触到水仙的香味,我的思想便回到那红对联,年夜饭,爆竹,红烛,福建蜜橘,早晨的道贺和我那件一年只许穿一次的黑缎大褂。”水仙花的香味让他想起家乡的萝卜糕,他特意去北四川路买了“二斤半一篮年糕”回家。吃着油煎年糕,水仙花的馥郁香味充满着屋子,最后,邻居的爆竹声让他从头脑和心志的心理冲突中惊醒过来——“它们是有一种欧洲人所不能体会的撼动中国人心的力量”。
他叫来自己的孩子:“阿经,拿去给我买些高升鞭炮,捡最响最大的。记住,越大越好,越响越好。”“于是我便在爆竹的‘蓬—拍’声中坐下吃年夜饭了。而我却好像不自觉的感到非常的愉快。”
禁令归禁令,老百姓还是按老规矩过自己的年。
林语堂拒绝过旧历新年,是有前因的。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宣布改用公历,并将这一天定为民国元年元旦;到了1914年1月,北京政府内务部提请“定阴历元旦为春节”。至此,原指阴历岁首的“元旦”和“新年”,被用来指公历1月1日,而阴历岁首改称“春节”——我们过春节,其实也只有100年历史。
在推行新历、废除旧历上,南京国民政府一度很激进。1925年1月1日起实施的《实行阳历新年的办法》规定,阴历新年之拜年庆祝等,均移在新年举行。1930年,国民政府重申:“移置废历新年休假日期及各种礼仪点缀娱乐等于国历新年:(一)凡各地人民应将废历新年放假日数及废历新年前后所沿用之各种礼仪娱乐点缀,如贺年、团拜、祀祖、春宴、观灯、扎彩、贴春联等一律移置国历新年前后举行。”
在这样的背景下,执着于旧历新年,被视为“不曰顽固,即曰反对民国”。林语堂这样自称“新派”的知识分子,当然要表示自己不过旧历新年的决心。然而,禁令归禁令,老百姓还是按老规矩过自己的年。“大都市的民众在‘国历’一月一日虽然要虚应故事,在大门上贴一副变像(相)标语的春联,而大门以内却若无其事,照常生活。一到‘农历’的腊月,小康之家从二十三日送灶起便忙碌起来,一直到正月十五夜元宵以后,才在筋疲力尽的情形下,结束了过年的变态生活。”记者伊弁在刊于《世纪评论》第一卷第六期的《过年》一文中这样写道。
1934年年初,国民政府停止强制废除阴历,不得不承认“对于旧历年关,除公务机关,民间习俗不宜过于干涉”。林语堂的《记元旦》写的就是禁令取消之后的第一个旧历年。巧合的是,一向表示不过年的鲁迅也在此时表示:“十多年前,我看见人家过旧历年,是反对的,现在却心平气和,觉得倒还热闹,还买了一批花炮,明夜要放了。”
你过你的年,他过他的年,不想过年也完全没问题。
尽管对待过年的心态各异,尽管不时出现“回家过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陋习”(罗永浩语)这样的激烈反对声音,年还是要过的。而社会在变,生活在变,人也在变,相应的,过年的方式也在变。
近年来,不想或者不敢回家过年的人是越来越多了。想开了,干脆不回家的毕竟是少数,更多的是想回而不敢回的,也就是所谓“恐归族”。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2011年春节前做的一个调查显示,41.1%的人认为自己是“恐归族”,而过年不想回家的原因,69.4%的人选了“不能衣锦还乡,面子上过不去”。
“恐归”的纠结在于,在理智上,知道春节很重要,父老乡亲盼着自己回去团聚;但情感上,实在不能接受回家后需要面对的一切:被问收入、被问有男/女友没、被问什么时候要小孩……反向思考一下,如果传统的“有钱没钱,回家过年”改成“不回家,照样过年”,是不是就可以不再纠结回不回家呢?
曾有人撰文提出:“恐归族”的诞生,“或者可以催生春节文化的新因子,如果合理引导,会更加丰富春节文化的内涵,使古老的春节焕发出新的活力”。既然“恐归”,那么,“不归”是不是可以成为一种新的过年方式?比如,带上父母出门旅游,一家人在路上,快快乐乐把年过了。或者把父母教育成姚志德、纪经书夫妇那样退休后环球旅行的生活家,他们玩他们的,你们玩你们的。
过年快不快乐,重要的还是心态。像鲁迅那样,一向不过旧历年,但在有了一定阅历,尤其是有了孩子之后,他心平气和地接受了这个节日:“今年却亦借口新年,烹酒煮肉,且买花炮,夜则放之,盖终年被迫被困,苦得够了,人亦何苦不暂时吃一通乎。”而且,你过你的年,他过他的年,以前不想过年现在忽然想过,没有问题;完全不想过年,也没有问题。就像梁实秋的父亲,在20世纪初期说出的话:“我愿在哪一天过年就在哪一天过年,何必跟着大家起哄?”
(编辑:瑞婷)
文章来源于互联网
研究人员选取了183名在校大学生为研究对象,并在麻醉状态下令他们的上腭患上溃疡。还对研究对象进行抑郁状况测试,并根据抑郁程度将他们分为两个对照组,随后对其口腔溃疡的愈合速度进行监测。 通常情况下,口腔溃疡的愈合时间为5~7天左右。但监测结果表明,与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