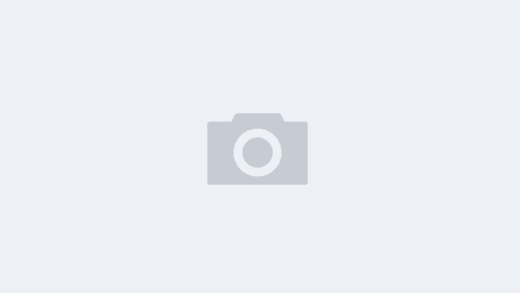2003年儿童节,我们能为孩子们做些什么?
我们这次的儿童援助机构的采访
跨越了4个国家和地区
从最繁荣的纽约街区,到最贫瘠的喜玛拉雅山麓
从罪犯的孩子,到生而智障的孩子
从尼泊尔泥石流的死亡线上逃脱的孩子
到那些在世贸双子楼的阴影下复苏的孩子
他们在儿童援助机构的帮助下
重新去寻找生命和幸福的可能性
我忘记了在采访中
哪个孩子对我说
受难是我们惟一的财富
我只记得那时候我的眼泪落了下来
北京示范儿童村
记者前去采访的时候,是个星期天。孩子们做完了功课,在院子里的草地上做游戏。
这个儿童村原先是个废弃的学校,房子很简陋,但功能还算齐全,建有阅览室、心理辅导室、电脑室以及文化活动大厅。孩子们的一切用度从床到褥子再到玩具、衣服都是社会捐助的。一进门的厅里放了一张乒乓球台,三五个男孩正在很认真地角逐。他们穿的衣服都比他们的身体大一号,但他们都是些不太臭美的男孩,所以穿在身上倒也自在。
儿童村美丽的女主人,28岁的武海燕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她是创办人张淑琴女士的第二个女儿。学新闻专业的她大学毕业后就投入了母亲开创的事业当中。“一开始时对母亲所做的事情不太理解,现在越来越懂得这份工作的意义。”
不一样的天空
童年的天空本该是晴朗无云,阳光灿烂的。天下父母无不想把最美好的世界给孩子,但对于这些孩子,他们遭受了太多所不应遭受的歧视,也比大部分的正常孩子更早地领略了人生的沧桑和阴暗。在他们童年所有的记忆中,有的亲眼看着父母犯罪,有贩毒的父亲常把毒品藏在孩子身上做掩护进行交易,还有的孩子亲眼见着母亲把粗暴的父亲置于死地……
但无论父母犯了什么罪,社会应该对他们的子女给予平等的教育和成长机会。理论上是这样的,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这样的孩子无不是在歧视和白眼中长大。很多孩子在被接到儿童村以前几乎是在死亡线上挣扎。刚被接到儿童村的孩子要么寡言木讷,要么反叛不羁,都带着曾经遭受严重心灵打击的印记。
儿童村里的一对兄妹,父亲因为杀害了母亲锒铛入狱。所有的亲人都抛弃了他们,母亲家的亲属更是视这两个孩子为仇敌。这对兄妹哥哥7岁,妹妹5岁,因为没有人给他们做饭吃,学校里从老师到同学的白眼和歧视使他们最终辍学。儿童村的工作人员找到他们的时候,两个孩子正躲在黑暗的茅草房里,哥哥手上尽是割草时镰刀砍伤的痕迹,而妹妹,正发着高烧躺在床上,奄奄一息。
“我恨警察,我长大了要报仇。”
他们当然只是些孩子,惟一不同的是他们的父母犯了罪,被法律带到了该接受制裁的地方。这是这个社会的规则,但这个规则在孩子眼中却是那么不可理解。“我恨那个警察,是他把爸爸带走的,我长大了要报仇。”6岁的小男孩咬紧牙关狠狠地说。作为一个孩子,他不懂大人的世界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他只知道是那个把父亲带走的警察改变了他原本拥有的生活,现在他的一切都变了。父亲犯偷窃罪入狱后,母亲很快另结新欢弃他而去,亲属们对这个没有劳动能力的孩子惟恐避之不及,结果他就这样过起了流浪街头的日子。对警察的仇恨渐渐转变成对社会的敌视,他没有生活保障,也只能靠小偷小摸过日子。幸好,他狱中的父亲写信给儿童村,申请代养他,才被及时接到了这里。否则,这个孩子极有可能重蹈覆辙,沦为新一代的罪犯。
儿童村的创办者,54岁的张淑琴女士从1996年在陕西自筹资金创办第一个儿童村时说:“这是个无辜而弱小的群体,同时又是一个有严重心理问题和犯罪隐患的群体。儿童村的教育要使在这种背景下的孩子和其他孩子一样健康成长,仅凭爱心是不够的,除了温暖,他们更需要知识,需要健康的心理,需要良好的素质,需要生活技能和谋生的手段,来帮助他们找到强大的自己。”
“我的理想是长大了去大饭店里洗碗”
来到儿童村的孩子们,都已经在附近的学校就读。这样,他们重新有了接受教育的机会,这对于他们曾是可望不可及的事。
同样的年龄,当别的孩子在父母的怀抱里撒娇,因为少了一件玩具而烦恼,儿童村的孩子却已经在学习如何分担大家庭的重担。因为没有专款,童村的许多生活开支都是靠自己解决。儿童村的后面是一大片菜地,里面是孩子们自己种的蔬菜,自己养的鸡鸭。顺义区政府还用低廉的租金租给儿童村几亩地种植果树,果子丰收之后卖掉换钱。
周末的时候,儿童村的老师会组织大一点儿的孩子上劳动课,孩子们平时吃的玉米和水果都是他们自己亲手种植的。艳阳天下,孩子们体验着劳动的快乐,更体会到生活的不易。
和孩子们聊天,最常规的提问是关于长大做什么。“我长大了要去大饭店里洗碗”,这个答案让我有点儿意外,于是我问她为什么是去饭店洗碗而不是干点儿什么别的呢?我知道自己心下期望她告诉我的是她想将来做个建筑设计师之类的。但这个小姑娘丝毫不明白我的善意引导,固执地坚持自己以后一定要去饭店洗碗。后来海燕给我解释说,儿童村经常给孩子们组织上劳动课,大一点儿的孩子去地里干农活,小一点儿的就去儿童村对面的饭馆帮着洗碗。这个女孩子很喜欢帮厨,所以,她的理想就是将来能到城里的大饭店洗碗,因为这是她现在惟一能做得比较熟练的工作。
“老师,我能叫你一声妈妈吗?”
因为这里的孩子在来儿童村之前都曾不同程度地遭受过他人歧视和虐待,所以,这里的孩子从不轻易提及过去,更从来不会用这个来伤害彼此。
但他们也想妈妈。儿童村的郝老师讲起一个细节,那天一个孩子怯生生地望着她仿佛有什么话要说,她走上去问她怎么了,孩子说出的话让郝老师的眼泪几乎要掉下来。她说:“老师,我想妈妈了,我能叫你一声妈妈吗?”老师一把把孩子搂在了怀里,孩子的小脸上是幸福的微笑。就这样抱了一会儿,孩子满足地走开了,蹦蹦跳跳地出去和其他孩子玩去了,而那句话却一直留在了老师的心里。
爱是孩子成长过程中最最不可缺少的营养,这些孩子,却在本该在母亲怀里撒娇的年龄失去了家庭的温暖。虽然儿童村也定期组织孩子们去监狱探望父母,但平日里点滴的爱又岂能取代。
一切热爱生命热爱这个世界的教育,他们都严重缺课,这堂课如果需要补的话,他们比正常家庭中长大的孩子更加需要爱。
菲是一位专业心理咨询师,工作忙碌,但每月都会抽一个周末去儿童村看望孩子们。面对着这样一群孩子,不能不让人百感交集。无论现在他们脸上的笑容是如何的灿烂,心灵深处都曾经历过阴霾漫天的日子。有的孩子恢复能力强一些,可以随着岁月的流逝和新生活的逐渐展开而忘记过去的伤害,性格比较内向的孩子则需要较长时间才能重新建立健康的人格和自信。
附录1: 北京示范儿童村
北京示范儿童村隶属中华慈善总会,于2000年12月在北京顺义正式建村。该儿童村是自筹资金,在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用集中供养、代养的方式,救助了一批因父母服刑而无人抚养的未成年人。让他们生活在相对比较温馨的大家庭里,以维护他们应该得到的生存权利、受教育的权利。
由于该儿童村孩子父母身份的特殊,儿童村经常上法制教育课,并定期带孩子们到监狱探视父母,以稳定其父母服刑情绪,增强其父母接受改造早日出狱与孩子团圆的信心。
香港有个匡智会
匡智会(前香港弱智人士服务协进会)于1965年成立,初期只为4名智障学童提供特殊教育服务。现在的13所特殊学校,按智障程度,3所面向轻度,5所面向中度,2所招收重度,还有3所是混合的,是香港最大的帮助智障儿童的机构之一。此外,匡智会还是全港专为智障人士服务的最大型非牟利机构,开设了58个服务单位,为约6000名不同年龄智障人士及他们的家庭提供服务。亚华所在的学校主要招收中度智障儿童。
亚华工作所属的机构是匡智会(Hong Chi Association),这是香港最大的帮助智障儿童的机构之一。在广东话里,匡是帮助的意思。匡智的涵义是不要着眼于智障儿童的缺陷,而要关注他们的能力,协助他们尽量发展潜能。
也许是跟智障儿童有缘分,在上中学的时候,亚华就去残障机构做义工,大学实习,她也主动选择智障幼儿园。她见很多孩子穿得很破很脏,她想,这些家庭一定很穷。可等到家访的时候,她才发现,这些孩子的兄弟姐妹都穿得整齐漂亮。她顿时意识到,即便在本来应该最温馨的家里,这些孩子也是被忽略的对象。
在这所特殊学校里,智障孩童主要患有自闭症和唐氏症。一般来讲,自闭症的孩子很难与外界有接触,不喜欢与人有眼光、言语交流,他们的语言表达很差,经常重复在别人看来没有意义的动作,他们的生活非常固定,即便是家具的摆放这样的小变化也会引起他们的恐慌。唐氏症则非常喜欢与人交往,和人非常亲密,喜欢拥抱、亲吻他人。
这两种孩子形成巨大的反差,前者需要用耐心打开他们的心扉,用热情将他们慢慢引入社会;后者则要告诉他们,亲密是要有界限的,比如说,男孩子就不可以随便亲女孩子的嘴。亚华选择了这份工作,在匡智会与这些孩子在一起。
小刚的故事
那是刚工作不久,我搭校车去家访,一蹬上车,就发现小刚一个人缩在汽车的角落,双手抱着头,脸涨得通红,一副不开心的样子。我走过去,想问他有什么不开心,可是没等开口,小刚迎头一拳,正中我的鼻梁。疼痛由鼻子直窜脑门儿,虽然没有流血,我的眼泪却控制不住流下来。两个人都愣住了。我上下摸了摸鼻子,心想,还好,没流血。 虽然鼻子很痛,我还是按原计划去家访。等实在受不了,才去医院。医生一见,有点儿埋怨,“你怎么拖那么长时间,你照照镜子,鼻子已经歪了,你就不怕破了相”。
那天,我彻夜难眠。在工作前,很多人对我说,要小心,那里有些孩子有行为问题。现在,我终于明白了,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可以胜任这个挑战。
小刚,14岁,自闭症,个子高,力气大,从外表看起来很正常,但经常在学校有破坏性行为,在家里,有时候用利器自伤。这是老师给我关于他的所有资料。
我开始给他做长达一年的心理辅导,每周三次。我运用一些游戏治疗的方法,让他在听故事、搭积木的过程中慢慢学会表达自己。我还跟他签订“做个好孩子”的合同。给他发一张日历,如果他表现得好,就让老师给他一颗星星。我们约定,一个星期如果得到多少颗星星,就给他小小的奖励。最初,要求很低,该儿童村的孩子在儿童村内可以生活到其父母刑满释放接其回家为止,对于一些父母刑期较长的孩子,他们将在儿童村生活到16到18岁。由儿童村对他们进行一定的职业培训,在他们掌握一定的技能后,与其所属社区有关部门共同给予妥善安置。等到他的情况比较稳定之后,我建议老师选他进纠察大队。小刚穿着特殊的制服,走在校园的时候,体会到一种成就感。3年后,他获全港弱能儿童最佳进步奖。现在,他毕业了,有一份自己的工作,但是每个星期还抽出一天到学校里面做花匠。
小强的故事
那是冬天,兰花绽放的季节,我第一次看到小强,他和一群孩子在追逐,不知道为什么,一下子,我心中觉得好亲好亲,看着他那双斜斜的小眼睛,我就喜欢上了他。我觉得他真的非常可爱,非常坦白,在他的世界里,只有黑和白。他的快乐和悲伤总是挂在脸上的,快乐的时候,飞奔过来拥抱你,悲伤的时候,悄悄地藏在小角落。可是,他又是容易满足的,不高兴的时候,你只要哄哄他,讲几句好听的话,表扬他,他很快就笑逐颜开了。
他来自一个单亲家庭,父亲很早病逝,母亲拉扯着他和他的两个姐妹。一个女人拉扯三个孩子在这个社会着实不易,母亲虽然爱他,但常常对他失去耐心。他就是生长在这样的家里,可是他还是那么没心没肺地快乐即便在本来应该最温馨的家里,智障孩子也是容易被忽略的对象。
有的时候,看着他,我有一种羡慕,我们平常人要怎样地修炼,才能得到那颗知足常乐的心呢?
我知道作为一名社工,要对每个孩子平等。可是,有时候,真的忍不住要有一点儿偏心。有时候,我会给他买一点儿好吃的东西,又怕别的孩子看到会嫉妒,就将他叫到一边让他慢慢吃。
别的老师,每次看到他来找我,总是打趣地说,你弟弟又来了。他的嘴巴也很甜,“姐姐”叫个不停。他是那种孩子,上课的时候,还算专心,跟他讲道理的时候,他也总是点头称是。可是一玩起来,他就得意忘形。他喜欢踢足球、打篮球,好胜心很强,有时候却又不能以技取胜,难免又推又拉又踢。打得过别人,自然得意洋洋;打不过别人,又要哭鼻子。那么多年,年年如此。
我很高兴,我可以陪伴他成长,看着他慢慢地长大。认识他的时候,他才6岁,一转眼间,他已经14岁了。
纽约纽约,我的英雄今年7岁
跨国际非赢利组织CYO基督教青年会,于 9・11事件之后,在纽约城外的普特南建立了一处小英雄营,旨在帮助那些失去父亲或母亲的孩子和那些遭受巨大心灵创伤的儿童。这些孩子的年龄大都在7~14岁之间,心理辅导和营队生活为期一年,目标就是让孩子们“return children”回归真正属于他们的童年。
小英雄的冒险游戏
冒险游戏的巨大木壁上写着大大的“FEAR”――恐惧,安全索已经布置好,孩子们躲在镜头的后面,仍然不愿跑到镜头前面来欣赏老师们的攀岩演示。
这是2003年的春天,普特南山谷儿童中心的小英雄营。
山谷之外,海湾战事初平,纽约和多伦多有SARS病毒在肆虐,小英雄营的2003年计划已经开始:FINDING NEW HOPE――寻找新希望。在这里,和平安静的普特南山谷,FEAR仅仅是字面上的假设,是攀岩游戏,可孩子们总有一天会面对真正出现在眼前的恐惧、战乱和生死。那一天,我们该怎么办?
小英雄营的计划开始于9・11之后,它把经历过双塔灾难的罹难者的孩子聚集在一起,进行了为期一年的心理重建计划。那是在美国Catholic Youth Organization 基督教青年会督导JEFFREY RUMPF的倡导下,与伙伴T.J.ROODE和CHRISTI DEROSA共同开展起来的一个儿童中心项目。
9・11事件后,CYO机构失去了近50名志愿者,大都是救生员和警察,超过3000名的孩子成为单亲儿童。
那年的秋天不鼓励笑声
看着那些在恐惧的噩梦中尚未醒来,谨慎言笑的孩子,该怎样做才能让他们在死亡、恐惧和突然袭来的灾难面前,仍然乐观有勇气,发现自己心底的力量?
“我们的辅导员和心理咨询师设计出三种最主要的治疗方法――让孩子们学会观察自己和表达自己;冒险游戏 ――我们需要小团员们去征服恐惧的野外挑战;最后就是Green Chimneys 首先倡导起来的动物辅助疗法 ――这对于那些总在怀疑自己存在价值的单亲儿童尤其有效。”JEFFREY RUMPF说道。
LOVE IN ACTION
而在其后的工作中,与第一批175名儿童营的孩子共同生活一段时间以后,儿童营的辅导员们也渐渐发现,许多经历创伤事件的单亲儿童在这样一个儿童营里生活了一段日子以后,也开始学习着重新寻找自己的快乐,心灵的安慰和辅救。
尤其是那些来自非洲、亚洲和巴尔干半岛,失去父母的孩子和那些曾经亲眼看到自己的兄弟和姐妹遭受不幸的孩子,他们和美国大都市的孩子生活在一起,种族的隔离和语言的陌生在这里都无形中消失了。在漫天漫地的游戏场中,在一堆颜料和肆意绘画的画纸中,陌生感和疏离感都不见了,孩子们从曾经的阴暗世界里争抢着逃了出来。
对于那些失去爱人的父亲或母亲来说,小英雄营的周末计划也给了他们一个机会。给48小时的完全家庭时间与孩子相处吧,世界上最爱我的人是谁?在小英雄营之外的“青年中心”周末计划里,很多孩子和母亲、父亲都找到了答案。
“我永远记得第一天来到CYO机构时,我的辅导老师送给我的那句话;Love In Action。后来我知道,这是CYO的警句,我想,小英雄营就是这样的一个行动吧,也许爱是需要慢慢发现,慢慢感觉的,但只要你愿意去做,去行动,爱毕竟会显示出来。” 艺术治疗师Amadou说, Amadou手中的鼓是西部非洲战士最偏爱的Djembe,浑厚的声音像是从一场丛林战争中传来。突然想起在耶路撒冷看见以色列的民间乐手演奏Dumbek的情景,《出埃及记》记载了摩西带领受难的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居无定所的40年流浪时光里,摩西将Djembe改良成小巧的Dumbek,以化解族人的恐惧和茫然。
鼓声在广阔的普特南山谷里,仿佛是送给纽约的古代奇迹。冷漠的城市似乎很难寻找可以给予孩子们的安全感和心灵的抚慰,所以“我们寻求最原始的心灵重建策略”,在小英雄营辅导员的计划里,回归山林与原始是最重要的一点。孩子们不仅要亲手去画出自己想像中的世界,而且要挑战自己心理的恐惧场景,最重要的一点是,让他们去到普特南山谷的“爱抚动物园”,这个“爱抚计划”中包括了许多种类的动物和许多需要皮肤接触的孩子。孩子们要学习着爱抚动物,学习着从抚摸的过程中感觉安全感的成长。
噩梦终于醒来
21岁的Bertan Selim,是来自马其顿的辅导员,他的回忆里有了许多前南斯拉夫战争的影子。
“你必须理解,为什么孩子们的心里对那些突然袭来的恐惧和噩梦难以接受,有时候你都在想,眼前发生的战争和死亡是一场噩梦吧,你只是手足冰凉,不知道该怎么做,只是呆住了,别怕,会有人来救你的,爸爸妈妈马上就出现了,他们马上就来把你摇醒,说!快!上学!三明治在便当盒里,牛奶在桌子上。但最终你会清醒过来,恐惧锐不可挡。你如此虚弱。”
Bertan Selim大笑着准备起跑,和小队员们一较劲。这是小英雄营每日的训练计划。
“就好像跑步的时候,你永远不可以依赖别人一样,我们要说服自己有勇气一个人跑步。从南斯拉夫出来以后,一直到成为这里的辅导员,我才慢慢感到,也许正是以前那一段经历,才使得我真正理解了那些孩子的心情。充满渴望地想与你接近,但又如此恐惧与人的接近。但我想,我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幸好,他们都很愿意和我亲近。”
在小英雄营的计划刚提出的时候,就有900多人纷纷报名希望成为志愿者,在经过一个专业的培训之后,他们才有机会被臻选成为小英雄营的辅导员。从而形成了目前小英雄营的基本比例:1∶9――1位辅导师面对9位儿童。
在Amadou的墙上,2003年7月后小英雄夏令营计划表即将展开。未来的小英雄营,为11岁~17岁的孩子专设的少年中心,在西点军校中开设Tailgate 派对,筹备加拿大多伦多市的世界少年日都将是这张计划表中的项目。
突然很想念在童军夏令营里的篝火、香甜的牧草,孩子们在逐渐恢复,重回童年的时候会不会再想起普特南山谷的牧草和鼓声呢?童年时所经受的伤痛与悲哀是容易被忘记的,还是容易被回忆的?
加德满都你的孩子现在好吗?
儿童之家,Namaste之家,尼泊尔贫困孤儿安全基金会和加德满都SOS儿童村是尼泊尔几个主要的儿童福利机构。就目前运作的成熟度来说,加德满都SOS儿童村是最规范的,也是规模最大的。
我们穿过乡间,正是加德满都盆地气温正好、和风吹拂的女儿节的黄昏。
我们的目的地是加德满都SOS儿童村。
但我们首先得穿过漫长狭窄的街巷,平静地接受面色黝黑的孩子大笑着追逐汽车的尾尘,接受他们抱着小小的婴儿弟弟或妹妹跑到正在休息的水牛面前蹲下来,探寻车窗里好奇陌生的脸;孩子们张望神色之外,加德满都城市之外,是起伏蔓的农田,荒凉的沟渠,悬满了喧嚣吵闹条纹色布店的老板正在招徕客人,手提抹红篮的女孩子在我们身边小心地走过。
女儿节是尼泊尔圣女的节日,她幸福到可以从深闺出来,呼吸到大街上的灰尘飞扬但却新鲜的空气,听到孩子们在广场上赤着脚奔跑和吵闹的声音。对普通的尼泊尔女孩、女人们来说,这也是一个从繁重工作中挣脱出来的日子,虽然她们歌唱的最主要旋律是为了未来的现在的丈夫祈福。
加德满都,孩子们的自由和梦想之都
我们似乎是跟着那些身着盛装的女孩子一起走进加德满都儿童村的,但眼前西方式的庭院结构和小小的洋房让我们很吃惊。孩子们正在庭院后的草坪上玩耍,一只魁梧的巴基度大犬乐呵呵地直冲到我们面前,这座养育了1200名孩子的儿童村是目前尼泊尔很先进很规范的一个儿童组织,也是救治孤儿和抚养儿童最有能力的一个机构。
看满院奔跑的大狗被孩子们洗得干干净净,总是很羡慕尼泊尔孩子可以光着脚,黑乎乎的小手,抓着大狗们的尾巴到处跑,可在儿童村,这好像会成为违禁动作。但我可以肯定的是,围墙之内的孩子都是幸福的孩子。手里的笔记本上还记录着尼泊尔官方公布的数字,尼泊尔14岁以下的儿童大约有340万人,约31%的孩子失去基本的受教育机会,35%的孩子正在作为童工被剥削。对尼泊尔的家庭来说,每家有五六个孩子是很正常的事,但夭折率却很高,而医院大都在加德满都,乡下只能用巫术来治疗。身在山国,每年还得承受58000多次的大小地震,平均每天就有158次之多,因而小小国家,孤儿也不少。更多的孩子是受不了家庭的虐待或拐卖和困苦,在8岁或更小的年纪逃到加德满都。对于他们来说,加德满都是他们的自由和梦想之都。
加德满都,究竟是谁和谁的梦想之都?究竟是哪一位天使走过田野,抚育漫天漫地的莲花和慈悲,却忘记了抚育喜玛拉雅山麓这些坚强却迷惘的孩子?
8个孩子的SARITA SHRESTHA妈妈
迎接我们到来的是儿童村妈妈SARITA SHRESTHA,从尼泊尔式的摇椅上站起来,经过静立在墙壁之上的印度教和佛教的神祗走到我们面前,问候Namaste。
我们突然的来访似乎惊扰了这个黄昏SARITA SHRESTHA计划中的女红工作。放下手中的刺绣棚架,她把孩子们从房前屋后拉了出来,向我们问好。SARITA SHRESTHA原先是一位销售店女孩,接受了系统的儿童教育和心理辅导课程之后,现在成了8个儿童村孩子的妈妈,转眼已经6年时间。
尼泊尔的女人和孩子有着一种坚持简单的勇气。前天的晚宴上,邂逅的女孩告诉我,尼泊尔人的一句笑谈名言,就是做尼泊尔男人和牛,因为他们都不用干活,而且有负责任的女人伺候和喂养。那最不幸的事情呢?
我没有问下去。谈话之间的突然沉默让我清醒意识到她也是一位受到尼泊尔文化影响的女孩,仿佛眼前平静单纯的SARITA SHRESTHA,她知道总有一天这些孩子都会离开自己,总有一天自己会老到叫不出孩子们的名字,现在,就是现在,和孩子们在一起,不用在女儿节上用心打扮自己,只需要在自己小巧的门厅树影下刺绣,是她这一生最开心最幸福也是最安宁的时光。
SARITA SHRESTHA朴实得甚至不向我们夸耀她是怎样把一个个孩子带大的,她也不去追究我们的到来有采访和拍摄的功利目的在其中,当我们问她,如果有一天孩子问你?你怎么办?
SARITA SHRESTHA疑惑地望着我们,似乎在惊异我们为什么会问出如此奇怪的问题。“他们不会问的!”SARITA SHRESTHA确定地说。
是啊,这些孩子早已经早熟到不需要询问这样问题的年纪了。经历了无数苦难、分离、被叛和不安全的童年之后,孩子们早就知道,可以拥有眼前和未来的安全,已经幸福到不去苛求一个完整的家庭和一位勇敢的父亲了,只要有一位勇敢善良的母亲就可以了。
天堂里的另一天
皇宫里尼泊尔圣女,儿童村的SARITA SHRESTHA妈妈,两个完全不同世界的女子分裂了这个下午我们在尼泊尔的视觉,很多吟唱的声音打断了我们和SARITA SHRESTHA的谈话,提醒我们这个不容忽视的“女儿节”。
庭院的空旷草坪上,一群十多岁的男孩正弹着吉他,It’s another day for you and me In paradise,Oh think twice……天堂里的另一天。那是在大学的暑假里去篮球场谈恋爱的音乐,但今天,它就在耳边,生涩的像永远的18岁的年纪, It’s just another day for you In this paradise,Just think about it。
附录4: 尼泊尔儿童之家
儿童之家建立于1989年,当年仅仅有18个尼泊尔孩子能够得到它的照顾。而今已经有105个孩子在它萌佑下的庭院中成长。儿童之家于加德满都的女院和位于Mahendranagar的男院大都遵循一种传统尼泊尔农业社会的教育方法,像种植、畜养以及一些初级学校课程和计算机教育。但儿童之家一直处于辛苦经营的状态之中,2003年他们的努力目标是能够在加德满都买一块真正属于儿童之家的土地,建造起属于自己的房子。
Namaste ――这是印度次大陆至喜玛拉雅山麓最温暖的一句问候,Namaste之家有鲜明的尼泊尔名字的特点,在2001年的4月由Cynthia Kennedy开始筹备,2002年秋天在博卡拉成立了完善的儿童抚养教育结构,目前有40名尼泊尔孤儿受到它的照顾,在一位管理者、行政主管和一位“妈妈”,两位“阿姨”(妈妈助理)的共同打理之下(接受的捐款和帮助大都来自美国)。
DOCSF-Nepal 也是一个刚建立不久的非赢利儿童机构,创立于尼泊尔的Sindhupalchowk地区。主要的目的是希望降低当地儿童的虐待和女童被贩卖情况。现在他们已经有能力将一些孩子从家庭虐待和被拐卖人手中拯救出来,这些孩子大都需要一定的心理帮助和较为安全的生活环境去保障他们的成长,他们大部分就读加德满都近郊的一所私立学校。
文章来源于互联网
心理健康是我们常常提及的一个词,近年来大家对这类健康也更加关注了,那么对大家心理健康认识有多少呢?什么样的心理是健康的,什么样的心理是不健康的,你是否了解?下面就为大家介绍几种心理类型:心理烦恼 心理烦恼是指有重大或者持久的心理刺激因素,或伴有不良教育及文化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