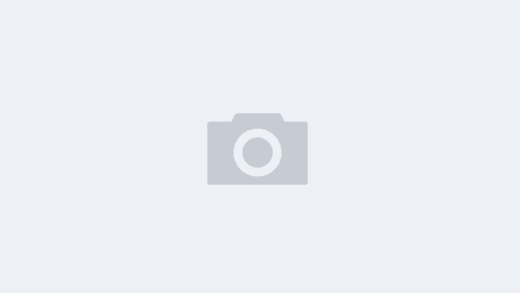因为腼腆,只有和家里人说话我才不会。在大学里,我说话不仅如蚊子一样小声,而且没说过一句完整的话,直至结识麦琪。大四上学期,麦琪到校刊编辑部。我编发过她十几篇文章,文字清新优美,语句灵动有趣。她的外貌更是比她的文章美得多,第一眼望见她,我油然想起维纳斯。那个周末,我悄悄从工艺品商店买回一尊维纳斯雕像。麦琪就坐在我对面,我不敢偷窥她一眼,却在她不在时,拿出藏在抽屉里的雕像浮想联翩。她问我为什么说话总低着头,我说我就习惯那样。她神秘而又直言不讳地告诉我:“有一件事,你可千万不要告诉别人,我耳背,听力差。我对编辑不熟悉,请教你时,你说话能不能大声一点?”我的音量达不到她的要求,她再次请求我:“你亮着嗓子,抬起头,看着我,让声音直接传送过来。你知道,眼、耳并使,听音的效果更好些。”面对这个弱聪者,我信心百倍地调整自己的心态,大声且一字一顿地给麦琪讲解一个又一个难题。她耳背得不轻,只有我说话连贯,她才会听明白,有时一句话我要说四五遍。她进步很快,不时以“犒劳”为由邀我到咖啡厅、麦当劳等公共场所。一个学期下来,我不仅说话不口吃,而且跟她的关系非同一般。
有爱的滋润,我变得开朗而活泼了。多年蕴蓄的知识如久旱逢春雨,顺畅地从我的笔下和嘴里喷涌而出,字字珠玑,妙趣横生,惹得女生们着了迷一样不断给我写情书。我悬崖勒马,躲避着她们,她们锲而不舍,不时制造一些莫须有的桃色新闻。那段时间,我走到哪儿,都能听到我跟某某女生如何如何的小道消息。平时倒没什么,可当我挽着麦琪从他们身边经过,听到他们也许是故意的交谈,我便心惊肉跳,好在麦琪耳背听不清,还很甜蜜地挽着我,冲有意向她传递信息的人微笑。
毕业一年后,我和麦琪结了婚。我拥着她坐在电视机旁,特意将音量调大,她感激地冲我一笑,说:“不用太大声,我听得清楚。”她把音量旋回到我听起来舒服的程度。我担心影响她男郎停复渭俪铺磺寰缰腥宋锏亩曰埃仕寄芩党瞿谌堇础?p>
婚后第一次到省城出差。第三天身体有些不适,晚上打电话回家,妻子马上听了出来,问我是不是了,说听着鼻音很重。放下话筒,我自个说话自个儿听,反复比较后才听出一点不同来,欣喜地再次打电话给她,说她耳力其实很好,我听不出来她都能听出来。她笑着说:“我这也不知怎的,时背时聪。”
她耳聪的时候,听力好得不可思议。孩子出生后依然一入睡就死沉的她,只要小床上的孩子有一点响动,她就会立马清醒过来。她一个晚上起床四五次,我全然不知。更绝的是,她能远远分辨出孩子的声音。对面陈家孩子晚我家孩子十天出生,同是女孩,此起彼伏地哭闹是常有的事。我跟妻子上下班总是一起来往,我多次听到她准确地判断隐约传来的哭泣声是发自哪家的孩子。
有了孩子,家里凌乱许多,我有时小声抱怨,妻子却从不跟我顶撞,但忙完手中的活,则会默默地收拾好房间。我不知道她是假装没听见,还是不跟我一般见识。多年夫妻生活,我发现了她听力的特别之处:凡有可能引起夫妻不和的话,她都听不太清楚;其他的,则耳聪目明。为了证明我的判断,一个周日,妻子到市场买菜时问我想吃些什么菜,我故意压低声调报了两道菜,中午饭菜上桌,我看到我报的两样菜,却蚊蝇般嗡嗡嘀咕道:“怎么没买荷兰豆?”她立即蹙着眉想,说:“你没说买荷兰豆呀。”“吝啬,还不是荷兰豆贵。”我故意板着脸说。她一点反应也没有,好像没有听到,微笑着给我夹菜,温言细语宽慰我:“明天一定买。”“算了,我不想吃了,吝啬。”我将音量提高一度。她火气上来了,将饭碗一放,喘着粗气,但却转而温和地说:“你说哪道菜冷了?我再去温热。”试验成功,我赶紧和颜悦色地说:“没事,我说排骨汤冷热刚好,你快吃,冷了就不好吃了。”我夸张地扒着饭,津津有味地说:“今天的菜炒得好,我喜欢!”妻子笑了,甜甜的酒窝灿烂着。
事后我想,大学时她说耳背其实是一个阴谋,但我希望她善意的阴谋发挥下去。
如今,妻子的耳背成了我和她的秘密。
文章来源于互联网,如有版权问题,请联系客服删除处理。
如果你觉得自己深陷其中不能自拔需要去咨询心理医生,那就去吧。我们常对看心理医生有一些偏见,觉得去看心理医生的人就是精神或心理有病(我们观念中的神精病)。但其实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在国外很多学校都会有心理治疗师参与到教学辅导中去,为的就是让孩子心理成长更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