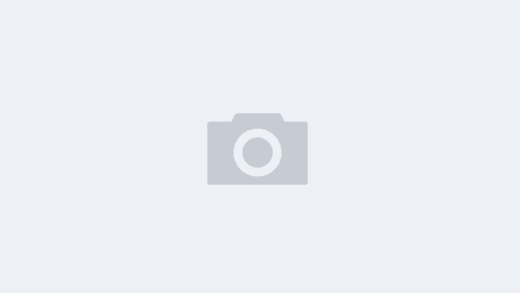・阅读提示・
自20世纪70年代提出以来,“斯德哥尔摩综合征”逐渐应用到包括针对妇女的家庭暴力、儿童虐待、人口贩运、战俘等很多现象的分析中。在《以爱求生》一书中,迪伊・格雷厄姆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一词,以此对父权制进行了分析。“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揭示了权力与情感之间的隐秘联系,也让我们看到不对等的权力关系所具有的复杂的表现形式,以及反对不对等权力关系的艰巨性。
“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源于发生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的一起绑架案。1973年某日,两名有前科的罪犯在抢劫斯德哥尔摩市内最大的一家银行失败后,劫持了四名银行职员作为人质。警方与劫匪持续对峙了6天,其间绑匪威胁人质性命,也对他们表现出一些善意和关照。令人不解的是,四名人质被解救后,却对绑匪产生了怜悯的感情,他们拒绝指控绑匪,并对警察持敌对态度,其中一名女职员还爱上了一名绑匪并在绑匪服刑期间与之结婚。这件事情激起了媒体和研究者的兴趣,研究者认为四名人质与绑匪产生感情,是一种认知紊乱的表现,在面对死亡威胁的情境下,人质为了求得生存,与绑匪之间形成了一种顺从、忠诚的感情,并将其命名为“斯德哥尔摩综合征”。自提出以来,“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得到极大关注,其使用范围也不断扩大,渐渐用于解释受暴妇女、受性侵和虐待的儿童、人口贩运等问题,也用于解释性别关系、种族关系等群体性政治,乃至用于解释国际关系。与之相应,对“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质疑和批评也一直存在。
“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内涵与应用
在精神病学和犯罪学的分析中,“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源于人质与绑匪面对面的接触中,绑匪掌握对人质的生杀大权,使人质产生了极度恐惧,处于极度无助、无力和屈服的地位,看不到逃跑和生还的希望。在这种情况下,绑匪所表现出的微小善意,甚至只是不殴打、虐待、强奸人质,就会赢得人质的好感。人质会对绑匪产生正向情感,对绑匪的立场产生认同,并会对警察等权威机构产生敌对情绪。“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表现是双向的,绑匪也会对人质产生好感,这被称为“利马综合症”。
在心理学的分析中,“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源于一种求生的本能,早期研究者斯特伦茨认为,受害者的求生欲望比对施害者的痛恨更为强烈,受害者与施害者之间产生的情感联系,是在压力条件下,自我的一种防御机制。塞西莉亚的研究则认为,这种情况在女性身上更易出现。针对“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上述特点,在心理学上也存在相应的精神或心理咨询,即帮助患者意识到他们的行为和感受源自人类遗传的生存技能,帮助受害者恢复正常的生活状态,减少他们受求生压力驱动的行为倾向。
自20世纪70年代提出以来,“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备受医生、研究人员、犯罪学专家、律师和媒体的青睐,被逐渐应用到包括针对妇女的家庭暴力、儿童虐待、人口贩运、战俘、恐怖主义、邪教、奴隶和妓女等很多群体的分析中。迈克尔・阿道扬等人对“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一词应用的扩展过程进行了研究,发现:1970~1980年代,“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仅应用于绑架和劫持事件中,1980~1990年代,“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应用范围有了扩展。通过将“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与“不对等的权力关系会产生错误的情感联结”这一观点相连,研究者逐渐认为,“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不仅存在于劫持事件中,而是存在于一系列权力不对等的关系中。在1994年出版的《以爱求生――性恐惧、男性暴力与女性生活》一书中,迪伊・格雷厄姆进一步扩展了“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应用范围,不仅用其来指代个体行为,更用其来解释“女性气质”这一群体行为。在这一基础上,“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又用于解释种族关系、国际关系和全球冲突等更大范围的研究中。
“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与性别权力分析
《以爱求生――性恐惧、男性暴力与女性生活》一书,是将“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应用于考察性别权力关系的重要著作。作者迪伊・格雷厄姆认为,在父权制下,男性的主导性权力使得女性一直生活在不被察觉的恐惧中,女性要时刻担心强奸等暴力的发生,也时刻害怕会惹得男性不悦。女性心理实际是在胁迫下所呈现的心理状态,是对男性暴力的恐惧之下的心理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女性常常努力取悦男性,也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产生了以顺从和牺牲为特点的女性气质。女性气质中包含了一系列取悦男性的行为,这与其屈从性地位有关,实质上是一种求生策略。
将女性的劣势地位归因为“斯德哥尔摩综合征”,这一观点看起来仍像是在“责备受害者”,实际上,迪伊・格雷厄姆也并未止步于此。迪伊・格雷厄姆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斯德哥尔摩综合征”(Societal Stockholm Syndrome)一词,转而将取悦型女性气质的根源转向了对父权制的分析和批评。在此基础上,迪伊・格雷厄姆也提出“社会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在所有压迫性的群体关系中都存在。
《以爱求生》一书出版后引发极大关注,有论者认为这本书是“20世纪女性心理学领域最重要的著作,阐释了包括受暴女性在内的每一位女性的经验”。这本书也为一些令人困惑的问题提供了答案,这些问题包括“为什么遭受暴力的女性难以离开施暴者?”“为什么有些女性比男性更能接受男尊女卑的观念?”“为什么女性总是害怕成为一个女性主义者?”“为什么女性比男性更不支持女性成为领导者?”“为什么霸道总裁爱上我的戏码总能拥有市场?”。
围绕“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质疑与批评
尽管有不少案例印证着“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存在,但其也一直饱受质疑。其中,最大的困惑在于“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是不是真的存在?既有资料表明,“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在所有劫持事件中所占的比例是很低的,根据2007年联邦调查局执法公告,只有不到5%的绑架受害者会发展出“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特征。至今,“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作为一个医学概念也未得到权威认可。由美国精神医学学会出版的诊断精神疾病的权威指导《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从来没有收录过“斯德哥尔摩综合征”。
此外,“斯德哥尔摩综合征”这个概念使用的不断泛化,也饱受质疑。迈克尔・阿道扬等人认为这是医学话语过度扩张的结果,将受害者贴上“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标签,意味着人们对异见的排斥,也是对受害者主体性和主观感受的贬低。
在笔者看来,“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之所以引发强烈关注,是因为其揭示了权力与情感之间的隐秘联系,也让我们看到不对等的权力关系所具有的复杂的表现形式,以及反对不对等权力关系的艰巨性。这一概念发展至今,其作为一个医学概念的有效性需要做进一步考察,但不失为洞察权力关系的一个有力的理论视角和分析工具。(刘天红)
文章来源于互联网
近年来,近视越来越常见,很多人早早就戴上眼镜,甚至有的小孩刚上幼儿园就开始戴眼镜。千万别觉得是危言耸听。2012-2020年,中国近视人口数量及增速不断攀升,中国近视人群高达7.1亿人,几乎有一半人都近视了。 图源:新京报有理数 虽然近视不是什么大病,眼镜一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