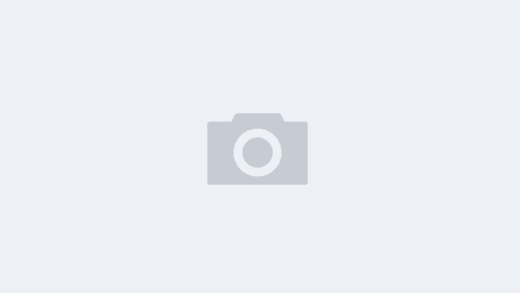佳亚特里·查克拉沃尔蒂·斯皮瓦克(GayatriChakravortySpivak)是印度裔美国人,于1942年2月24日出生于印度的加尔各答市一个中产阶级家庭。1963年她赴美国康奈尔大学读比较文学专业研究生,后师从“耶鲁学派”大师保罗·德曼攻读博士学位,因翻译德里达的《论文字学》(OfGramma-tology)而出名,成为解构主义在北美最重要的阐释者和传播者。她在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研究等领域也取得了骄人的成就,是美国重要的文学批评家、思想家,也是一名重要的教育家,尤其以研究属下(subaltern)教育问题见长。现在哥伦比亚大学比较文学与社会中心工作,任哥伦比亚大学阿瓦隆基金会讲座教授。近年来,斯皮瓦克先后执教于许多大学的讲台,足迹遍布全世界。她的教育思想在美国甚至世界上都有很重要的影响,对我们中国的当前教育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斯皮瓦克教育思想主要关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有关发达国家高等教育的大学课堂教学的问题,另一方面是针对第三世界贫困人口的扫盲运动。斯皮瓦克认为,这两个方面看似泾渭分明,实则是相通的。
一、斯皮瓦克的大学教育思想与西方的人文主义传统
斯皮瓦克强调人文学科教育对于人的培养具有深远的影响,因此认为在现代大学中人文学科的地位不容动摇。通过教育塑造人是西方自从古希腊以来的重要传统,尤其以文艺复兴时期为盛。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强调培养“完整的人”,即通才,而不是只学会了某种技艺的“专才”。斯皮瓦克捍卫这种人文主义的传统,认为当代的大学教育不应该等同于技术培训,或仅仅面向市场,而应重在塑造完善的人。
对教育非功利性的强调在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莱昂纳多·布鲁尼那里就得到了强调,他认为人文学科的目的是使人成为完整的人而不只是一个学者(专家)。英国著名教育家红衣大主教纽曼在《大学的理想》中提出自由教育的主张,指出教育是为了培养理智自身而不是为了某种特殊的目的,也不能屈从于职业培训。这与德国教育家、柏林大学创始人洪堡的“纯知识”思想一脉相通,后者认为不应该考虑社会经济、职业等种种实际需要,大学教育要注重培养想象力。
人文主义教育传统在斯皮瓦克那里被坚定地继承下来,并成为批评的武器。在市场的影响下,美国各大学出现了削减人文学科经费、裁减人文学科教职、许多人文学科专业关停并转的趋势,这令斯皮瓦克这样的教育家痛心疾首。作为一种对策,许多学科开始跟市场结合,以图扭转被吞噬的局面。在斯皮瓦克看来,这是代写论文一种短视行为。她指出市场不是人文学科的出路[1](Pxii),大学教育不应该只是教会人如何去做生意,去挣钱[2](P126),否则,我们的教育就太可悲了。
大学课堂在她看来,无疑应该是非功利性的,但却应该是政治性的。她认为教育具有很强的政治性,因为谁都无法超越政治。而同时,教学和研究却要去政治化,要扫除偏见和制造不友好的政治。另外,一个人的学术研究和其社会实践活动分不开。教育不能忽视边缘群体,不能忽视种族、性别、阶级的问题。高等教育课程中的女教师应该起重要的作用。总之,斯皮瓦克认为,理想的大学教育应该培养和塑造具有完善人格的人,与他人之间充满友爱的人,期待着民主到来的(democracytocome)人,对属下不抱偏见、不以西方为中心,并且时时准备为他者做事(toworkfortheother)的人。
斯皮瓦克一贯强调文学尤其是文学在大学教育中所起到的重要的作用,其中最主要的是体现在想象力的培养上。同时,在大学教育中,如何教会人们一种“生活的知识”(livingliteracies)而不是“杀人的知识”(killingliteracies)是一个重要的问题。“生活知识”的教育是一种不带任何偏见、超越种族隔离、不以自己的标准去强加别人的教育,而“杀人知识”则是相反,充满了偏见和强加[2](P126)。人文学科,尤其是比较文学,教会的是“生活的知识”,而不是“杀人的知识”。
斯皮瓦克的大学理念与德里达的“无条件大学”观点一脉相承。从1983年在美国的《大学在今天是否有‘存在之理’》的专题讲演,到《职业的未来或无条件大学》(2001),德里达多次表明,大学理念应该抗衡拜金主义和工具理性,大学应该是‘无条件大学’,其核心应该是人文学科。
《一个学科之死》(DeathofaDiscipline)是斯皮瓦克受德里达晚年思想(尤其是他的《友爱的政治学》)的影响而写成的一部著作。其中,她多次阐述了她的大学教育理念。斯皮瓦克强调教育对人的教化作用,希望自我向他者敞开,去接纳他者,同时也让他者进入自我。
二、属下教育问题(贫困人口教育问题)
斯皮瓦克对教育的讨论频繁出现在各种访谈和文章中。她一直把自己定位为一个属下阶级的教师,在美国高等教育课堂之上大声疾呼要让属下阶级说话。在教学之余,她积极参与属下的教育启迪工作,深入到第三世界最贫困地区的最破旧学校,不仅培训教师、教授课程,还努力把那里的贫困孩子们带到公共领域之中,让他们进入现代社会。
巴西教育家保罗·弗莱雷(PauloFreire,1921-1997)在贫困人口教育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以著名的扫盲教育实践模式“费莱雷方法”而闻名于世。其教育理论不仅在第三世界引起了很大反响,对发达国家下层阶级的教育也具有深远的意义。弗莱雷发表于1970年的《被压迫者教育学》(PedagogyoftheOppressed)迄今仍然被人们认为是50年来教育界取得的最高成就之一。斯皮瓦克经常在演讲和文章中谈到弗莱雷,他们有许多共同之处。两个人都是从第三世界到美国,并在美国著名大学中占有教职;同样关心第三世界的受压迫者,谋求从教育方面下功夫来改变这些被压迫者的命运。只是他们对这些被压迫者的称呼不一样,弗莱雷用的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术语“被压迫者”,而斯皮瓦克用的是葛兰西的术语“属下”。
弗莱雷和斯皮瓦克都因为“不好懂”而受到许多批评,然而,文字的不好懂只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并没有影响他们理论的广泛传播。马萨诸塞大学人文和教育学教授马纳尔多·马塞多指出,这种不好懂与语言晦涩实际上关系不大,因为尽管学富五车的学者常常抱怨看不明白,而“16岁的男孩和贫穷的‘半文盲’妇女”却能轻易地理解其复杂的语言和思想并产生共鸣”[3](P12)。他为弗莱雷辩护说,文章不可能写得平白易懂,这样的无理要求只能使文章黯然失色[3](P13)。斯皮瓦克的语言也常常被人认为是晦涩难懂,但是,《斯皮瓦克读本》的选编者指出,在做完一场演讲之后,她不仅得到了听众的持续喝彩,还在一群“不是来自当地的大学,而是来自底特律的社区的非洲裔美国妇女的簇拥之下走向接待处”[4](P3),而其中一位妇女捧着一本翻烂了的由斯皮瓦克翻译的德里达的《论文字学》,她的女儿则手持斯皮瓦克的《在其他的世界里》(InOtherWorlds),这是她的中学课程必读书[4](P3)。弗莱雷曾经指出被压迫者如果得不到好的教育,一有机会就会成为次压迫者[3](P46),斯皮瓦克深感这个观点的正确性,她致力于把它运用到自己的理论研究和实践中。她对恐怖主义的分析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她重视对属下教育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如果属下得不到好的教育,只要有机会,他们就会去压迫比他们地位更加低下的人。她指出,在伊斯兰世界中经常出现的妇女、儿童充当人体炸弹,造成巨大平民伤亡的事件,恰恰是这些“属下阶级”没有得到好的教育,而被邪恶势力利用、威逼和洗脑而造成的[5](P96)。他们受人唆使而成为了牺牲品,也伤及无辜。教育者的责任就是要通过“非强制性地对受教育者的欲望进行重组”(uncoerciverearrange-mentofdesires),让属下阶级进入现代社会公共领域,用通行的方式捍卫自己的正当权利。
在教育者与被教育者的关系问题上,斯皮瓦克和弗莱雷都强调对话。弗莱雷当年讨论的教育者是革命领袖;而斯皮瓦克说的只是普通的知识分子。弗莱雷认为,革命领袖不应该利用被压迫者的依赖性来从事斗争事业,而应该通过对话来发动群众[3](P20-1)。通过对话,革命领袖说服被压迫者要进行斗争,而被压迫者也把这种意识内化为自身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然后再投入行动。对话起到关键的作用,而不是利用被压迫者的情感依赖。而斯皮瓦克在谈论与属下关系时,提倡知识分子带着对他者的伦理责任与他者对话,达到一种对话和交流。知识分子还要对他者敞开自己,尊重他者的伦理独特性(ethicalsingularity),期待他者的回应。要意识到属下是一个个具体的个体,具有差异性,不可把他们看成铁板一块,因此对属下的教育要有针对性。一味灌输是不行的,要双向交流,要通过教学向属下学习。她认为知识分子不是属下的领袖,与属下的关系是平等的;虽然自己参与被压迫者的教育和引导,但自己从来就不是领导,教学只是向属下学习的手段。
在具体的教育方法上,斯皮瓦克也或多或少地借鉴了弗莱雷。弗莱雷最重要的教育方法在于“生成主题”,即激发被压迫者的批判意识。他反对传统的“灌输”式教育概念(‘banking’conceptofeduca-tion),认为其“把学生的创造力降到最低甚至抹杀其创造力,并使学生轻信,灌输教育的这种能力符合压迫者的利益”[3](P26),而提倡“提问”式教育(‘prob-lem-posing’education),认为它是一种人道主义者和解放的实践,强调被统治者必须为自身的解放而斗争。他指出提问式教育有助于克服权威主义和理智主义,使教师和学生成为教育过程的主体[3](P36)。与此相似,在教育方法上,斯皮瓦克一贯反对单纯的背诵,认为这样的教育会破坏学生的心智和他们的创造性[6](P148),而“教育要使所教授的内容内化”[6](P149)。她所谓的背诵并不是我们理解的为了准备考试而进行的快速记忆,而是指在属下教育中经常采用的只让学生背诵,却不给他们讲解所背诵的内容,结果造成学生对学习内容并不理解,背诵之后很快忘记,因此根本就达不到教育的目的的机械方法。她重视人文教育,因为“人文教学是抗击帝国主义的最好的最持久的武器”[6](P140)。要想在属下中推行民主教育,首先必须改变他们的思维习惯,而不是教会他们数学或者科学[6](P142),她一再强调的所谓“非强制性地对其欲望进行重组”就是这个意思。她指出,她只对一对一的认知改变感兴趣,因此反对社会运动,认为在世界各地“共产主义失败的原因在于没有针对属下的主体性,只组织了社会运动”,这些针对集体的运动太快了,而且“社会运动对教育的兴趣从哲学上讲太浮浅”[6](P153)。这种教育是长期的,不可能立竿见影,但是意义十分重大。斯皮瓦克和弗莱雷在“阶级”这个词语的运用上也有相似之处。尽管二者都坚持阶级并没有在现代社会中消失,还具有很重要的意义,但是,他们都不把阶级看成是一个机械的、同一性的、一成不变的、没有差异性的东西。在反殖民斗争中,在《被压迫者教育学》里,弗莱雷坚持阶级分析的立场,这种立场在后期的作品中也一再得到强调。但是,他重视用聚合的理论框架来进行压迫分析,“在这个理论框架中,压迫的对象是受诸如种族、阶级、性别、文化、语言以及种族地位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因此,他反对任何把多种因素简化成单一因素(包括阶级)的理论分析”[3](P5)。
斯皮瓦克也在一定程度上坚持阶级分析方法但是,她的属下概念具有差异性,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团体。她认识到,在印度,被压迫者阶层由多种不同的集体组成,种姓、宗教、地域、文化、以及社会经济地位的差异导致他们具有不同的政治诉求,不可能形成同一种固定的阶级意识,也就无法用同一种声音说话。在属下教育问题上,斯皮瓦克尤其重视属下妇女的教育。她质疑印度“属下研究”(subalternstudies)历史学家们对女性声音有意无意的忽视,认为她们与同属被压迫阶层的男人相比,因为经济地位的低下和性别关系上的从属性而被双重边缘化。她反对一切形式的二元对立,但是却策略地使用“女性”、“属下”、“阶级”等这些概念。总之,斯皮瓦克吸取了不少弗莱雷的理论和经验,又加上自己的解构的研究方法和女性主义的视点,使自己的研究更有深度,更有说服力,是把抽象的理论与具体的社会实践相结合的典范。三、大学教育和贫困人口教育的相通之处在斯皮瓦克看来,大学教育和贫困人口教育这两种教育形式看似差别很大,实则具有相通之处。因为,无论是哪种形式的教育,其作用都在于对被教育者进行非强制性的欲望重组。“非强制性的欲望重组”是斯皮瓦克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术语,其中包含两个关键词“非强制性的”和“欲望重组”。教育应该是非强制性的,这似乎已经成为定论。但是,当今的中国教育界在少儿读经问题上不同的看法似乎又重新引入了非强制性和强制性之争。自由主义者认为,教育应该是非强制性的,而保守主义者则认为需要有一定的强制。当然,在这里不可能展开这个问题的讨论。而斯皮瓦克的观点非常明确,教育必须是非强制性的,这与意识形态和宗教灌输不同。
斯皮瓦克和传统的人文主义者一样,建议把教育与宗教的教化作用分开。宗教究竟应该是强制性的还是非强制性的,这也不是一个新的话题。早在宗教改革年代,马丁·路德等人就认为,宗教不应该是强制性的而应该是劝导性的。这似乎也能解释旧约中的上帝和新约中的上帝的不同。《旧约》中的上帝严厉有余,对不忠诚者睚眦必报;而《新约》中的上帝仁慈有加,永远期待着新信徒皈依和迷途者知返。在宗教改革者看来,宗教的作用是启迪、劝导,这与国家的惩恶扬善不同,国家靠的是剑,即武力,而宗教是靠信仰,也就是布道、美德和主动接受。通过国家和宗教作用的二分,把政治从宗教之中分离出来。然而,至今还有不少宗教是强制性的。斯皮瓦克在谈“恐怖主义”时指出,有些宗教流派是通过强制来吸纳并管理会众的,如原教旨主义。穆斯林世界的人体炸弹就是受了这种强制性的教育的结果[5](P93)。对被教育者进行“欲望重组”是教育者的职责。斯皮瓦克提倡对属下进行非强制性的教育,目的在于把属下引入公共领域,通过当今世界通行的方式例如法律来捍卫自身的权利;通过进入主流社会、发展经济等等方法来摆脱属下的处境,从而实现自我解放。而不是像原教旨主义那样,通过强制来控制人,最终使他们误入歧途。斯皮瓦克不止一次谈到自己帮助贫困的印度边远地区的孩子写申请想要得到一口水井的事情,作为教他们如何进入公共空间和捍卫自身权益的例子。对大学生来说,教师的作用是帮助他们成为一个完善的人,一个政治上正确、又对人充满友爱的人,一个获得生活的知识的人。教育者对被教育者进行“非强制性的欲望重组”的最好的方法就是人文教育。斯皮瓦克认为要想达到获得生活的知识的目标,在教育的两极都需要人文教育。对于贫困人口来说,长远来讲,人文教育是抗击帝国主义最好的武器:人文教育可以培养他们的思维习惯,让他们能够想像与自己属下处境不一样的公共生活;通过进入公共空间而逐步实现社会流动,从而摆脱属下的地位。对于美国的大学教育来说,人文教育可以使学生摆脱自己的西方中心论,摆脱对属下的偏见,真正做到尊重他者。也就是说,通过人文教育,可以在富有者和贫困者之间构建一个共同体,一个相互对话的平台,从而形成一种真正的友爱关系,期待一种到来的民主。
作为解构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斯皮瓦克颠覆了西方/东方、第一世界/第三世界、大学课堂教育/扫盲教育等这些二元对立中对前者的推崇和对后者的漠视,认为教育不是专业培训、不是给予人谋生或者发财的工具,而应该以人为目的,塑造人、教化人,从而达到全世界人与人之间的友爱,达到世界大同的美好理想。她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又针对时代的发展提出了有创建性的教育理论,并且身体力行。
四、斯皮瓦克教育思想对中国教育的启示斯皮瓦克把教育视为是一种解放属下阶层的方法,通过教育使他们走上公共空间,从而实现社会流动。对于属下,帮助他们的最好的方式不是通过宗教或者社会运动(革命),而是通过教育。教育是“授人以渔”而非“授人以鱼”。教育者和被教育者不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而是平等的关系,教育者也可以向属下阶层学习。十几年来,斯皮瓦克经常利用假期在孟加拉、中国云南的穷山僻壤最贫困地区的学校培养教师和学生。她还一贯强调,要想做好属下的教育,必须学习至少一门属下的语言,要注意差异性,要尊重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文化和历史。为了搞好教学,她还学习了广东话和普通话。
斯皮瓦克的大学教育思想很有代表性,她所谈到的大学教育问题在中国也普遍存在。比如说在经济大潮影响下,中国的人文学科陷入困境,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经济金融等热门专业,而文、史、哲等学科成为冷门。市场的冲击在某种程度上左右着中国的大学教育的课程设置,人文学科往往被认为“无用”而被改造并设置“有用”的课程。然而,人文学科对人的教化作用不可低估。斯皮瓦克指出,人文学科可以作为社会科学有益的补充;在大学里,人文学科的地位不应该动摇。
她的属下教育思想对中国贫困人口的教育也有重要的启示意义。特别是她的教育是引导人走向公共空间的理论,对中国的贫困人口的教育很有针对性。建国初期,我国就很重视农村人口的扫盲问题,当时就编写了一些把法律、政策融入授课内容的浅显易懂的课本,在教人认字的同时,也把一些公共领域的东西印刻到人们的头脑之中去。如今,我国虽然全面推行义务教育,还立志建立社会主义新农村,但是,落后农村人口的教育仍然存在很大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究竟应该怎样提高这些贫困人口的素质就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我们尤其需要借鉴斯皮瓦克的对话理论,教育者应该通过与贫困农民交流对话来了解他们,“知识分子还要通过教学向草根学习,通过教学去了解他们”[2](P126),同时也对自己的不足有更深的理解。
斯皮瓦克一再强调,在教育中,最需要重视的是人本身。她多次引证康德关于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的观点,指出要尊重这些贫困人口,切不可没有调查研究就把自己的观念强加给他们。在《国际框架下的法国女性主义》(FrenchFeminisminanInternationalFrame)等论文中,她激烈批评了乐善好施的西方女性主义者臆断属下女性的思想,认为这实质上在某种程度上与剥削压迫这些女性的势力形成了一种共谋关系。斯皮瓦克这种以人为本的精神和对属下妇女的关注态度尤其值得我们学习。
谈到斯皮瓦克与中国教育,她更加看重的似乎还是贫困人口的教育问题。直到2006年3月终于来到北京接受清华大学特聘教授的殊荣之前,她曾经有过多次机会来北京或上海,但她都没来。例如她拒绝参加1995年在北京召开的世界妇女大会,因为她反对这些非政府组织,反对花巨资做秀,认为这种大会对属下妇女没有任何帮助,广大属下妇女根本没有参加的可能,也无从受益。在此之前,斯皮瓦克两次作为志愿者到过中国云南最穷困的地方,为当地学校教授英语。斯皮瓦克声称自己是旧式的共产主义者,重视思想的改造,她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告诫众人:贫困人口最需要的并不是经济上的援助,而是观念的改变。
斯皮瓦克的理论对中国的教育者和研究者也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即教育者和研究人员要谦逊地把自己的优越当成不足;要学会向属下学习;要警惕利用自己的地位自以为是地替属下说话,结果反而让他们无法发声。可喜的是,她的这些观点已经在戴锦华、李小江、艾晓明等中国学者身上得到一定的体现,已经开始对中国的学术界起到指导作用。
[1]Spivak,GayatriCharkravorty.DeathofaDiscipline[M].NewYork:ColumbiaUniversityPress,2003.
[2]Spivak,AtBothEndsoftheSpectrum[A].LightOnwards/LightOnwards[J](123-136),2002.ca/fulltext/ltonword/p1B.htm.07-04-10.[3]保罗·弗莱雷.被压迫者教育学[M].顾建新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4]Landry,DonnaandGeraldNacLean,eds.TheSpivakReader:SelectedWorksofGayatriCharkravortySpivak[C].NewYorkandLondon:Routledge,1996.
[5]Spivak.Terror:ASpeechAfter9-11[A].Boundary2[J]Vol.31:2(81-111),2004.
[6]Barlow,ToniE.NotReallyaProperlyIntellectualResponse:AnInterviewwithGayatriSpivak[A].Positions[J]Vol.12:1(139-163),2004.
文章来源于互联网
甩头和捋头发的动作可能有两种来源,一是因为头发长了,会遮挡住视线,因此人们会下意识地向一边甩头或者捋头发。二是模仿别人,这一般发生在青少年身上,影视广告中的酷男靓女甩头发扮酷的动作,很容易成为他们模仿的对象。 时间久了,这个动作就可能成为一种习惯。一些…